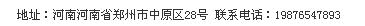注意事项
拿什么拯救你
寻找质朴生活,回到安静阅读:点击上方"读书村"↑订阅
璇璇的摄影
拿什么拯救你
文
细草
鸽群掠过城市的上空,在每一个清晨或是黄昏。城市的晚钟永不止息地行走在轮回里,时光滴滴答答,如戏的人生一幕又一幕。
很多时候,医院像一架沉默冰冷的摄像机,生的喜悦,病的无情,死的悲恸,离的伤怀都聚焦于它的法眼。此生从医,无可选择地面对太多的生死无常和人间疾苦,这里是尘世的苦难所,更是心灵的修炼地。
1
“原始粒细胞的细胞核就像沙子里面打鸡蛋,原始红细胞的细胞核像鸡蛋上面洒沙子,原始单核细胞的核染色质就是一片柔曼的薄纱,你要用脑,用眼,用心去鉴别。”12年前,在陕西省血液病研究室里,我的恩师魏旭仓,一个拥有满腹人文情怀的骨髓细胞形态学专家,带我走进了七彩斑斓的细胞形态学世界,领着我亲眼目睹了白血病对生命残忍狰狞的摧残。
那个20岁的小伙子刚从西北大学毕业,入职体检时意外查出白细胞大量增多,经魏老师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没关系,你们尽管用最好的检查和治疗,钱不是问题,我家亲戚都在美国,不行我们就去美国治。”他的母亲骄矜凌厉地说,似乎儿子的病简单的如同一场不起眼的感冒。“我们会尽力的。”我的恩师用不卑不亢,平静而坚决的语气回答她。他是那样慈悲,每一次都用最轻柔娴熟的双手为小伙子骨穿,活检,镜检,“他还这么年轻......”他总是一边看着显微镜一边喃喃自语。那段日子,似乎我们都相信,生命有无限的可能性,小伙子一定会康复。然而,没有等到那个骄傲的母亲带儿子走向美国,那年国庆长假的第二天,小伙子的生命就令人猝不及防地戛然而止。
那一天,秋雨淅沥,我陪着恩师值班。静静地坐在实验台边,看着一滴滴泪珠从恩师的眼角滑落,我理解,那是一个善良的医者对生命无力拯救的无奈和伤感。秋风吹过来,穿过沉默的实验室长廊,掀起桌面上骨髓报告单那一页页纸张,像一只天空伸来的手,抚慰着世间生离死别的伤口。
两年后的春天,我端着采血盘穿梭在医院血液科病房,为这里的血液病患者检查他们的外周血细胞形态。在这个汇聚了来自天南海北的血液病患者的病区,失血的面容,苍白的手指,长满血泡的嘴唇和因为频繁化疗而掉光的头发是我每日司空见惯的事物。浮华褪尽,这里不再背负世俗一切名利头衔,神木的煤老板,吴起的特级教师,黄河滩的打渔人,城中村的农民都称对方为病友,保命,是他们心底唯一的,最迫切的愿望。
她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姓李。40来岁,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化疗使她满头乌发掉的一根不留,她很开朗,自嘲地叫自己光头李。看得出,她的丈夫很爱她,每次去病房,眼前这个斯文的男人都在为妻子擦拭着身体或是喂食着汤羹。“周医生,你来啦!”她笑意盈盈的声音像是要在阳光下放飞揣在怀里的鸽子,让人有片刻的错觉,这不可能是一个患有绝症的白血病患者。
她告诉我她过去的幸福,孩子懂事,老公体贴,经济丰裕,游历过很多地方;她送我自己亲手制作的铜铸的开瓶器,上面的铜车马栩栩如生,像要御风而行。她开心地憧憬着即将进行的骨髓移植,她的姐姐已经在层流洁净病房等待着她,手术费用将近50万,为了治病耗尽积蓄可他们不在乎,有人就有一切。她发着光的眼睛饱含着春天的气息。我微笑着谢过,告别,打心底为她祈祷手术的顺利。
两周后的周二,我再去病房,她的病床上空空如也。“她搬到几床了?”我问邻床的病人家属。“上周五晚上就走了,临走时一直在喊她不想死,我们实在听不下去了,我把娃带到别的病房住了一晚......”家属红着眼睛说。
她死于急性骨髓移植排异反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免疫学现象,供受双方的白细胞抗原的差异程度决定着排异反应的轻重。她一定没有想到,亲姐姐的骨髓,依然没有救得了她的命。
至今,白血病依然没有很确切的病因。化学接触,病毒感染,最常见的基因突变都是患病的原因。谁也无法预料哪一天,染色体上的基因会不会突变,在无法预知的宿命里,生命脆弱的像一只玩具。医学可以让我们拥有一双慧眼,识破血魔的真容,却未必有一双回天之手挽留生命。每想到我们都只有这么一个无法回头的人生,我都深感人类是如此孤独渺小。生命只是一段流光,生是借,死是还,该怎样好好去拥有,才是我们最该思考的问题。
2
又是一名百草枯中毒的患者。
24岁的女孩,仅仅因为一次拌嘴或一点不顺,还没来得及品尝生活的甘醇和爱情的甜蜜,就亲手把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路。他的男友医院,看着他焦渴的眼神,我能感觉到他急切的期盼,站在生与死的边缘,生命是海天片羽,有太多无法承受之轻。
百草枯之毒至今无药可解,这种农用除草剂不足10毫升就足以致命。短期内病人没有什么大的症状,但它会一步步使人的肺部纤维化,最终气竭而亡。而医生能做的唯一只是减轻痛苦,减缓病程,却无法改变人财两空的结果。
为女孩化好血浆,ICU的护士对着我叹了口气说:“唉,她的男友强烈要求我们救治,可我们也只能尽力送好她走完这最后一程。”
这一世,生命要经历多少磨难才能功德圆满,感情要经历多少洗礼才能静候花开。善与恶,仇恨与热爱可以互不排斥地并存于同一颗心里,一念之间的选择,能成就一个人生,也
能毁掉一个人生。
另一个黄昏时分,急医院,急救单架抬下来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吸毒者,在家里因毒瘾发作而失控发狂,用剪刀戳破了自己的股动脉。我去急诊室为她采血,她长得很美,三十开外的年纪,皮肤白皙,身材修长,面容姣好,黑发如瀑。她的股动脉伤的很深,止血带捆扎已难以止血,两个护士正徒手按压着她的股动脉为她压迫止血,鲜血瞬间浸红了她们的橡胶手套。破损的股动脉像一根爆裂的水管,紧绷的高压使得血液象喷泉一样奔涌而出,血花四溅,油然而生的恐惧深深笼罩了我,顷刻间,这个苍白的女人,血压骤降,命悬一线。
我无法想像意志崩溃的那一刻,她是用多大的力量挥剪自残,但眼前这猩红的伤口分明展示着一个生命的绝望无助。我无从知晓是什么蛊惑她沾染上万恶的毒品,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闯进来,闯进人生的泥沼,闯进无力自拔的深渊。
这世界有太多的诱惑包围着我们。如同一只只沾满毒汁的草莓,摇曳着醉人的皮相,散发着香甜的气味,一次不慎也许就会令人万劫不复。无论是饮鸩自绝,还是挥剪自残,自我的沦丧谁也无法拯救。
3
年夏末,我的左耳又一次患上突发性耳聋。30年前,我正上初二,右耳突聋,听力剧降,少年不识愁滋味,庆幸还有左耳支撑着这个有声的世界;30年后,再遇劫难,左耳和世界隔起一道厚厚的高墙,双耳患病,我的心沉入了焦灼和痛楚的苦海。所有积极的治疗收效甚微,高频的耳鸣令人无法安眠。核磁,CT,喉镜,电测听,耳鼻喉科的冉主任为我一遍遍的筛查和诊断,她是一个幽默干练,德技双馨的好医生,每次看着满面愁容的我总能用一句简短风趣的话四两拨千斤地消弭我心中的阴霾。中西医结合,针灸,熏蒸,为了恢复听力我拼了全力,寻遍了西安的耳鼻喉专家,独自一人不远千里去国内最权威的上海复旦大医院求诊,最后的结果依然如同最初冉主任诊断的那样,我必须要接受听力下降的现实,战胜失聪的恐惧和焦虑,坚持服药,调整心态,乐观面对。每一次求诊,我都在专家诊室哭的像个孩子,那一刻,我不是一个医生,丢掉厚厚的盔甲,所有的不甘心,不情愿,不服输都在我潸然的泪花里流淌着。“别害怕,双耳都生病了,你还能听的见,你要相信这是很幸运的!就算以后听力越来越弱,助听器,人工耳蜗,我们也有的是办法让你听见!”耳鼻喉专家邱建华微笑着安慰我。80高龄的王锦玲教授编纂过耳鼻喉科教材,她像一个慈祥的母亲,手把手教给我一套“耳保操”。我是一个患者,与他们素昧平生,因为我的眼泪,他们都捧出一腔大医的博爱,用温情体恤着我,关怀着我。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缓解,总是去安慰。”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早已是医界名言,是的,受伤的躯体需要治疗,受伤的心灵更需要疗救和指引。
漫长的治疗过程,因为耳疾,我开始渐渐安静下来。当和外部世界的喧嚣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内心的大门真正为自己敞开,我忽然发现,这些年来,那个真实而纯粹的自己早已迷失在尘烟里,面目皆非,满目疮痍而浑然不自知。那些身体康健的日子,生命如繁花满树,却被自己秋月春风等闲度,虚掷浪投了太多的光阴。如今,回首所来径,苍苍横翠微,8月,蝉声如雨,淹没了我的耳朵,一场暴雪覆盖我的世界,宁静是单纯的原色,雪上燃烧着生命之火。听不见这个世界的喧嚣怕什么,重要的是我的心需要重新活过,用心倾听自己的声音,倾听花开的声音;身体的病痛算什么,一滴水便存千江月光,世法何须尽尝,重要的是,这滴水,是否有情,有爱,有向往光明的追求,有奔流不悔的志向。
4
舞台上,歌者孙楠在深情地演唱:“我拿什么拯救,情能见血封喉,谁能把谁保佑,能让爱永不休!”
任正非在尼泊尔对自己的员工慷慨陈词:“每个从泥坑里爬出来的人,都是圣人!”
俞敏洪在波士顿的夜景里提醒自己的合伙人:“乔布斯说过一句话,记住你即将死去。人的一生追求的不是长度和宽度,恰恰是深度,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到底做了些什么,为自己带来了什么,为家人带来了什么,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
此刻,我听见自己的心在说,自救才是生命坚强的核心,爱是生命最大的救赎。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愿你与这个世界深情相拥。
细草,原名周茜,医生。发表有诗歌散文作品等。现居西安。
点下边标题阅读作者最新文章:
·她的静安里,她的城……
读书村dushucun—鲜活·有质地·接地气主持人:丁小村
联系
qq.擅长白癜风疾病的诊疗白殿疯症状初期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