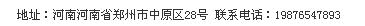当前位置:耳聋>>注意事项>>拉维诺之歌,是对当代非洲社会的弊端,>>
注意事项
拉维诺之歌,是对当代非洲社会的弊端,
它的确是拖在后面的烟雾之母,一个疯子,一个戴草帽的人,天空晴朗,它却制造烟雾,风和日丽,它却搅起云团,弄得我们一身漆黑;干芦苇投入了篝火,浓烟滚滚,火花四溅。
像口头传统中的赞美诗人一样,卡其拉对火车作英雄般描绘时,试图掺入一种微妙的抗议或否定:火车是个恶毒的、黑色的小东西,它带走了我的兄弟,从此杳无音信,我愤愤不平,泪水溢满了眼眶,如河流般沿着脸颊淌下,我站在那里悲伤地痛哭!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描绘的是现代技术的产物——火车。尽管卡其拉用他的本土语言(索托语)写作,并且同索托颂词的传统保持着联系,但选择了一个现代主题,来证明这种传统的适应性以及同现代生活持续的相关性。
乌干达诗人奥考特·庇代克在歌中记录了类似的成就,最著名的是《拉维诺之歌》。直到年去世,奥科特一直坚信口头传统的生命力。他的一些同事——包括塔班·罗·利庸(TabanloLiyong)——抱怨,和西非相比,东非还是一片文学荒漠,而奥科特却回答道,塔班这样的批评家都患上了某种文学耳聋症。
尽管奥科特去了英国几所最好的大学(布里斯托,牛津等),但还是坚定保持着与当地阿科利族传统的联系,致力于本土信仰体系的研究和口头文学的翻译。即使用英语创作诗歌,他也尽可能贴近阿科利语的各种形式,为的是证明本土传统中有足够的资源,来处理任何题材。
《拉维诺之歌》是奥科特的第一次尝试。他用阿科利语创作了名为《维帕拉维诺》(WerpaLawino)的诗歌;但为了增加发行这一点,或许和卡其拉一样。这首诗是社会批判作品,紧紧仿效阿科利谴责诗歌(poetryofabuse)的传统。
一个年轻的女人(拉维诺)抱怨和谴责受过教育的丈夫(奥科尔),因为他为了时髦的都市情妇(科勒门蒂娜)而冷落自己。她的谴责不但针对丈夫及其情人,还指向将丈夫从成长的传统中夺走的西方文明。如赫伦(Heron)所揭示的那样很快便翻译成英文。
虽然这首诗的英文翻译未能充分捕捉阿科利语原作的抒情之美,但奥科特还是尽可能贴近了传统的语调和意象。比如,拉维诺描述奥科尔和科勒门蒂娜之间的亲吻时,流露出了粗鲁和轻蔑。你像白人一样亲吻她的脸颊,你像白人一样亲吻她张开的嘴唇,你们像白人一样从彼此的口中吮吸那黏糊糊的唾液。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非洲传统诗歌的重复结构。赫伦指出了这首诗如何密集地借用了阿科利传统诗歌的意象。例如,在文集《爱的号角》所记录的传统诗歌中,奥科特有一个长矛的意象:锋利坚硬的长矛让它劈开那花岗岩我信任的长矛让它劈开那花岗岩猎人已经在荒野中沉睡我将死去,哦!
在《拉维诺之歌》中,这个意象带着强烈的回声反复出现,直到诗歌的结尾,拉维诺敦促她的丈夫与本土传统的持续性力量(sustainingforces)实现和解。乞求它们的谅解请求它们给予你一根新的长矛一根有着锋利而坚硬矛头的长矛一根可以劈裂岩石的长矛求得一根你可以信任的长矛。
拉维诺的抱怨是对当代非洲社会的弊端提出的抗议,无论对于所嘲笑的西方文明,还是所支持的传统,这些抱怨都振聋发聩。讽刺的语调非常有效;奥科特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当地的语言表达方式完全能够从主角所选的视角,来表达新的观点,再现新的习惯。
口头文学传统的改造和利用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但值得注意。在改造的过程中,传统的内容和形式都清晰可辨。举例来说,图图奥拉在作品中呈现的奇幻世界,与口头传统中的故事多有相似之处。
在《阿南西瓦的婚姻》(TheMarriageofAnansewa)中,骗子还是叫阿南西(Ananse),蜘蛛网偶然会进入股市的场景之中,这有助于渲染主题——即骗子的狡诈导致了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然而,对口头传统元素的利用中,现代作家是有选择的。现代作家的表现形式和口头传统的关系是有限的;即使用的都是熟悉的人物,但人物身处的是陌生环境,或是变化了的关系秩序。
吸引作家寻求口头传统帮助的,与其说是表演的物理因素,不如说是包含其中的基本观念——人们认为这些观念具有持久的相关性。着不同程度的微妙性。其中一个层面可以从钦努阿·阿契贝的小说中看到。
虽然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伊博族的社会现实(过去和现在),也看不出阿契贝本人按照任何我们所知道的寓言故事来组织小说的结构,但他仍然在作品中运用了许多口头文学传统的内容和技巧。其中之一是谚语。在《瓦解》中,他告诉我们:在伊博人中,交谈的艺术受到高度重视,谚语就是词语被吃掉时蘸的棕榈油。
因此,在阿契贝以伊博族为背景的小说中,当人物(特别是成年男性)进行对话时,会非常自如地运用这些精心选择的俏皮话,来为他们的语言润色。
谈话或公开演说的艺术不仅以大量使用谚语为标志,也以有选择地运用故事为突出特征。阿契贝的《神箭》(ArrowofGod)中,传统文化和欧洲文明之间的对抗造成悲剧性的紧张氛围,而书中不时出现故事和歌曲,特别是休息的间隙——妇女和孩子们晚间坐在院子里娱乐,这些故事和歌曲给紧张氛围带来了必要的喘息。
下面这段展示了伊祖鲁(Ezeulu)在与两名族人的高谈阔论中,如何使用谚语和故事讲述氏族里一个任性儿子的命运,从而以解释性寓言的方式,阐明了一个道德教训。伊祖鲁直到最后才开口说话。他沉默地向乌姆阿诺(Umuaro)致敬,神情悲痛。
乌姆阿诺克崴努!哼!乌姆阿诺欧波都尼希克崴努!哼!克崴祖埃努!哼!我们吹奏的芦苇被碾碎了。两个集市日之前,正是在这里,我讲话时用到过一句谚语。我说,一个成年人在屋里,就不能把母羊系在绳子上分娩。
当时,我在对奥格布菲·伊戈瓦勒(OgbuefiEgonwanne)说话,他就是屋子里的成年人。我告诉他,他应该发言反对我们的计划,而不是将一块烧红的碳放到孩子的手掌上,吩咐他小心拿着。我们都已看到,他是怎样小心拿着的。当时,我不仅对伊戈瓦勒一个人说话,而是对这里所有的成年人,他们舍弃了分内之事,却做了另一件事。他们留在房子里,母羊却遭受分娩的痛苦。
曾经有一位伟大的摔跤手,他的后背从来没有着过地。他从一个村庄摔到另一个村庄,把每一个对手全都摔倒在地。于是,他决定去找众神摔跤,同样得了冠军,打败了每一个前来应战的神。有的神长着七个头,有的是十个,但是他把众神全都打败了。他的同伴吹着长笛,唱着赞歌,请求他离开,但他拒绝了。
人们恳求他,但他的耳朵被钉上了。他不但没有回家,反而发出挑衅,要求众神派出最优秀、最强壮的摔跤手应战。所以众神派出了他的保护神(personalgod),这个瘦小的神仅用一只手就抓住了他,然后猛地把他摔倒在布满石头的地上。
乌姆阿诺的人们,你们想,父辈为什么要给我们讲这个故事?他们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想告诉我们,不管一个人有多强壮、多伟大,也绝不应挑战自己的保护神。这就是我们族人的所作所为——挑战自己的保护神。我们给他吹奏长笛,但是并没有祈求他远离死亡。
现在他人在哪里?没人提供建议的苍蝇只会跟随尸体进入坟墓。但是,让我们先把阿库卡利亚(Akukalia)放在一边;他已经照自己神的命令去做了……从上文例子可见,尽管阿契贝有选择地运用了民族的口头文学资源,但是,当表演的物理因素出现在他所借鉴的传统中时,我们仍然可以看见。然而,在更为微妙的利用层面上,这些因素并不那么显而易见。
事实上,现代作家利用口头传统的基础在于,他们能认识到时代变了。尽管在文化自豪感的驱使下,他们认同本民族的遗产,但是当代生活的痛苦事实——尤其是当传统自身呈现出作家未必认可的世界观时——迫使他们以一种同传统保持或远或近距离的方式,重新组织这些文化遗产。无论如何,在这一层面上,口头传统转向了比喻或象征性的运用,而非原样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