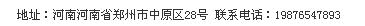当前位置:耳聋>>治疗原则>>小说大世界城市肿瘤外两篇>>
治疗原则
小说大世界城市肿瘤外两篇
雷琼,女,生于年2月,湖北省监利县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荆州日报》文学副刊编辑。著有文集《太阳花开》,小说、散文、诗歌散见于各报刊杂志。
从病房到手术室是一条生与死的漫长之路。幽暗的楼道那么寂静,孟飞有一种通往坟墓的感觉,他被推进一间同样昏暗的手术室,一丝阳光透过浅蓝色的窗帘射向他,这是上帝对他最后的触摸吗?几位白衣天使忙碌起来,要他放松心情,马上就好了,现在开始打麻药了。这一切多么像临终祈祷,但他并未得到些许安慰,无尽的孤独袭来,他感到越来越冷,仿佛陷入绵绵的黑暗之中,不一会便失去了知觉。但他隐约听见肚子被划开的撕裂声,听到脏器被掏出的声音。他如一具丢失灵魂的僵尸,任人解剖与围观。
……
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
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
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
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
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留在在这春天里
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
请把我埋在在这春天里春天里
汪峰的歌从遥远的地方飘来,这是孟飞最喜欢的歌。他拼命想睁开眼睛,想用手抓住什么,但无力的放弃了,仍然是无尽的黑暗,什么也抓不住。他想,这一定是来到另一个世界了。
“飞哥,飞哥,我看见你动了,你醒了吗?”狗子将手机音乐调小“就知道你喜欢这首歌,只要听这歌你就来神。”
他握住孟飞的手,骤然间接踵而来的大悲大喜,让他有点失控。医生说如果手术,生与死各占百分之五十,术后能醒来就算活了。
“拌——妈——日——的,痛——”孟飞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无比虚弱的字,把狗子乐开了花。
“医生!医生!快来呀,他醒了!醒了!飞哥飞哥,你死不了啦!你又活过来了!”
周教医院的顶极医生,在欧洲留学多年,他的医术誉满省内外。慕名而来的病人让他有干不完的活,他曾满怀悲悯地说,医生越忙越证明这个世界还不那么美好。
周教授来到孟飞病床边,一张如来佛的脸绽开微笑“认得出我吗?”并细心查看孟飞手术后的情况。
孟飞努力地点点头还想说什么,被周医生制止,要他好好休息。
他从护士手里接过病历时说“手术很成功,但要细心护理,不能出半点差错。”又温和地对狗子说“你不愧是他的好兄弟!继续加油!稳定他的情绪,好好看护!”
他早已忘了孟飞刚入院时对他的粗暴无理。
那天门诊,周教授看了孟飞的化验单,望着这个手臂刺有青龙的年轻人,想用合适的语言向他陈述病情。孟飞最初还算镇定“您就直说吧,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没关系,我承受得起。”
周医生温和而宛转地说“别急,你先住院吧,还需进一步检查才能确认,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会尽力医治”
孟飞急了“怎么还要住院?那还检查个卵,你就说这几项查到什么了?”
周教授严肃地说“血小板少!红血球少!血红蛋白少!三少!淋巴出了问题!必须住院!赶紧住院!”
孟飞愣了片刻,转瞬就失控了。
你是说我得了淋巴癌?放你的屁!你看我多结实,你是吃干饭的吧?医术TM不行吧……
老子哪有时间住院,还好多事等老子去处理……
老子怎么会得癌!是想黑老子的钱吧……
陪同来的狗子拉住孟飞“哥,你冷静点!听医生的!再闹别怪兄弟我不客气!”一把将他按在椅子上,孟飞止住了骂声,低下头用双手抱住,发出轻微的啜泣声。
周教授以他的经验与修养,没有再对孟飞说话,不动声色地写病历与入院单,让孟飞尽情发泄,这是一种绝望的表现。从医这么多年,他什么人没见过?那些绝望的病人要么死一样的沉寂,要么伤心欲碎或猛兽般的愤怒。但任何状况都丝毫影响不了他对病人的拯救。他问狗子是孟飞什么人,要求通知孟飞的家人。狗子说“我是他兄弟,他家里没靠得住的人了,我可以对他负责!”
能把一匹野马束缚在病床上实属不易。孟飞在一家信贷抵押侦探公司任老总,是个大忙人,忙业务、忙各种酒店会所的应酬。几天的吊瓶、抽血化验、穿刺检查等,已把他的坚硬的锐气磨砺了一半。总有电话打来,请示这个女人要怎么处理、那笔款子要怎么办,他怒回“老子现在海边度假呢,你们看着办!别跟老子整出么事来就行!哎哟——疼——”
电话那头问“孟总,您怎么啦?度假应该很爽怎么还疼呢?”
他没再回话,把手机丢在一边。他向正在给他做穿刺检查的周教授哀求“您行行好,让我出院好吗?真他妈的活受罪!”
“不能!我不治好你,你出去坚持不了多久,再来找我就不是受罪这么简单了!”
周教授心想,这个混小子不知死活,已病入膏肓了还想着出院。这几日的各项检验,淋巴瘤诊断已明确无误,病灶在脾脏上,要尽快切除阻断扩散,否则性命难保。但病人还在浮躁中,必须让他静下来配合治疗。他与狗子详谈过,孟飞年幼时母亲就去世了,跟着酒鬼父亲艰难度日,十多岁就混迹街头,狗子比他小三岁,境况也好不到哪去。狗子说,“从小孟哥就照着他,把他当亲弟,他没用,总是饥一餐饱一餐到处流浪,但孟哥有本事,一弄到钱就去找他,带他买衣服上馆子。自从他出任这信贷抵押侦探公司老总后,就招了狗子去管事,这才有了稳定的生活。他说“孟哥就是我亲哥,一帮兄弟都靠他养活,您一定要治好他,我听您的!”
周教授看了看狗子,说“你要做到让他不受任何干扰,能安静治病,行吗?”
“行!我这就去公司,安排好他的后顾之忧!”
对于狗子所说信贷抵押侦探公司,这类名称含糊暧昧的公司,周教授似乎早有所闻。在光天化日与霓虹灯交错的夜幕下,踩着法律的红线赚昧良心的钱,像城市的肿瘤,在某个阴暗角落蔓延。但他是个医生,他只能治肉体上的肿瘤。为了与死神赛跑,他昨晚一夜没睡,根据孟飞的病情制定了精准的治疗方案:立即外科手术切除脾脏,再进行化疗。
孟飞在白底黑字的化验单面前终于安静下来。周教授说“也不是那么可怕,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配合治疗,还是可以治愈的。你年轻,身体底子好,要有信心!”周教授的话给他绝望的心照进一丝希望之光。他接受了现实,在生死各半的时刻,他突然想起酒鬼父亲与前女友小柯,他们曾对他说过相同的话“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再不回头就晚了!”只是没想到报应来得太快了。想到自己做过的烂事,也该死有余辜了。
他二十多年的人生,从未被命运之神宠爱过,他只不过是一只被蜘蛛网束缚的可怜虫。他的公司背后真正的老板是老瘤,他的老大。他只是老瘤的一颗棋子。老瘤在这个城市拥有酒店、富人俱乐部、高级会所、KTV酒吧多处,那些有钱的客户,衣着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另一个灵魂,往往在豪华的遮羞布下暴露无疑。老瘤善于在这些人身上寻觅啄食,用美酒、女人、毒品、赌场等,赚取他们同样来历不明的白花花的银子。当客户快被榨干时,就推荐给孟飞的公司去借款,高额的利息让他们抵押了公司、房产或者又受贿去了。老瘤的大额进帐就是这样玩来的,孟飞则收获剩下的汤汁。这就是老瘤设计的游戏,在这座繁华城市的一角天天上演。
但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这个公司还承担其它的业务,比如借款后不能如期还款的女孩,就推荐给老瘤,大多女孩进了那里就走上了不归的风尘路;不能如期还款的男孩则被老瘤的有关部门培训,变成他的又一颗小卒,在那些场所为他赚钱。但孟飞始终留有底线,不逼迫不强制,只是推荐。
孟飞这个扯淡的公司,员工大多是招聘来的三无人员,无毕业证、暂住证、结婚证,他们挣扎在社会的底层,如一群蝼蚁。穿上工服后,他们就变得人模狗样了。只有小柯是前台一道亮丽的风景。在一次公司的年会中,孟飞与小柯都喝醉了,他们为各自的痛苦干杯,孟飞说为他的酒鬼父亲把他母亲给喝死了干杯!小柯说为她的父亲与别的女人好上了干杯!最后他们就拥抱在一起了。酒醒后他们便恋爱了。
那是孟飞二十六年灰暗人生中的唯一亮点,小柯是他的一缕阳光,照亮了那年的春夏秋,但到了冬天,小柯还是走了。他们时常吵架,都是为公司那些不正当的业务,用小柯的话说,赚这样的钱简直是失去了良知!她一直想改变孟飞,劝他走正道,与她一同离开这里。而孟飞却说,等再赚一大笔钱就与她结婚。小柯说,我可不会花这肮脏的钱!孟飞也怒了,骂她蠢货!那天小柯哭着走了,消失在雪花飘舞的大街上,从此杳无音信。
周教授下的判决书,使孟飞变得颓靡不振。手术前周教授握住他的手,传递给他一丝温暖与力量,他本想给周教授道歉,眼睛却不争气地湿了。周教授说“狗子跟我说你是硬汉呢,我相信你不会害怕,你可要挺住,一定会好的,你还欠我一个道歉呢!”在这几天的接触中,他被这位涵养深厚的中年教授所吸引,他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东西让他彻底折服,如果有来生,他一定做像周教授这样的人。
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
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
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
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
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
……
汪峰的歌声再一次把孟飞唤醒。这次他彻底清醒了,知道自己从手术室出来后真的没死,周教授没有失言,果真没让他死。他想不通,一个做尽坏事的家伙,周教授为什么拼命拯救他,像他这样的人治好了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好处?
肿瘤切除后,接下来便是化疗。当五颜六色的药液流入他体内时,那种翻江倒海让孟飞生不如死。周教授送给他一本小说《生命之光》,让他转移注意力减轻痛苦。于是他开始看小说,没想到他被书中人物迷住了。主人翁生活在美国中部的小镇,少年时离家出走,误入黑道,跟随老大干尽了坏事,成年后,他渐渐觉醒,决定除掉这些城市丑恶的肿瘤,经过周密的策划,作出了一个惊人举动,后将这个最大的黑道窝点端掉了,回到家乡成为人们的骄傲。
周教授查房时,孟飞就与他讨论书中情节。周教授说,这就是作为人性的光辉!主人翁心中那缕微弱的阳光终于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几个月后,孟飞痊愈了,出院那天,周教授一直将他送到温暖和煦的阳光下,孟飞有点不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您是给我第二次生命的恩人,也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的人。我为最初进院时对您的粗暴无理道歉,对不起您!我真是个混蛋!”
“我也因你又获新生而有了成就感!加油吧,希望你越来越好!”周教授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孟飞没有先回他装修豪华的家,他和狗子买了烟酒,还有很多吃的东西,直接把车开到酒鬼那。两年多来,他第一次来看他,平常只是派狗子送钱来。他看到酒鬼背更驼了,人更老了。他曾经那么地恨他,恨他喝酒,恨他使妈妈离去。现在他一点都不恨他了,他与狗子将东西搬到屋里。酒鬼见到他们便步履蹒跚地走来,满口酒气地骂道“这是哪个狗日的,还晓得回来啊,你冒死得外头,冒遭报应啊?”
狗子连忙劝道“叔,别生气,他这不是回来了吗?他也蛮不容易的,您看都瘦了一圈了。”
酒鬼睁大他醉迷迷的眼睛,扫了一下孟飞,对狗子说“么搞成这个鬼样了?”
见狗子不做声,孟飞便说“还不是多亏你天天咒我,菩萨显灵了!我遭报应了!差点死了!你满意了吧?”
狗子说“叔,飞哥只是病了一场,冒得么事,现在好了。”
酒鬼便不作声了,抱着酒瓶喝酒去了。孟飞与狗子帮酒鬼收拾完屋子,准备回孟飞的家。酒鬼却口齿清楚地吼道“你哪天真要死了就死到屋里来,别死在外面做孤魂野鬼!”
狗子见到飞哥捂着红了的眼睛,急步向门外走去。
孟飞感觉自己完全变了,狗子也说他变成一个新人了。似乎周教授摘除肿瘤的同时,还给他的灵魂埋下了别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正在发芽。孟飞戴上狗子给他买的样式很酷的帽子,无比振奋地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与狗子一同露出了快乐的微笑。
老瘤打来电话,责备他总不见人影,说有一个大单,要与他在酒吧面谈。昏暗的灯光下,老瘤并未发现孟飞的异样。他说钓到一条大鱼,是某厅长养情妇与受贿的资料,北上广等有数处房产,海外有大额存款,这次你要亲自出马运作,以最快的速度尽量多捞到钱。
孟飞爽快地答应,一定按大哥的指示办!多谢大哥的关照!
让老瘤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在电视里看到他的鱼落马的消息,这次他颗粒无收。
又过了一久,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吸引了周教授的眼球:公安部门挖掉了本市最大的涉黑团伙,黑头目老瘤旗下的所有娱乐场所与公司全部被查封,市民们为铲除这个城市肿瘤而大快人心。
周教授笑了,心中闪过一丝快意,正如他摘除病人肿瘤时的那种快意。
《年夜的歌声》
雷琼,女,生于年2月,湖北省监利县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荆州日报》文学副刊编辑。著有文集《太阳花开》,小说、散文、诗歌散见于各报刊杂志。
妈妈说“唱完这支歌,春天就到了!”说这话时,最小的弟弟刚学会唱《小燕子》。
那年冬天非常寒冷,太阳没有丝毫的温度,只徒增耀眼的白光。广袤的平原变成无际的雪原,鸟儿早已没了踪迹,门前的长河结了厚厚的冰,长长的冰凌挂满树枝与屋檐上。这样的冬天可把我们乐坏了!小伙伴们忙着堆雪人打雪战,在冰河上奔跑打滚,或看冰层下静止的水草,猜想鱼儿们的去向。
别人家的孩子可一整天在外野,而我们家不行,我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将弟妹们带回家。在堂屋,父亲早已升起树蔸火向,八仙桌上四方各放了纸笔,砚台放在正中。这是我们假期必做的书法课,他希望我们中能出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但我们都毫无兴趣,每每鬼画桃符,把纸祸完后,就去玩烧烤大餐。我们个个都是烧烤大王,糍粑鼓而不糊,鱼要香而酥脆,连骨吃的,团子要烤熟透带脆皮。这是在火向边的最高境界。我曾怀疑我们的职业是否都错了,原本应该去开烧烤店的。
父亲对我们很失望,看来没一个是书法家的料。好在他老人家英明,订了《长江文艺》、《大众电影》等杂志,还买了很多图书,专治我们假期多动症。但疗效还是不佳,一不小心,弟妹们便遛出去了,我也借口找他们去,一去也疯玩的没了踪影。
曾经有一个夜晚,我偷听到父母的窃窃私语。
“看来这五个孩子没希望了,他们在学校不好好读书,成绩考的这么差,但对文学与书法都不感兴趣,只晓得玩儿,唉!以后怎么生存!”父亲叹息道“老子做死做活的,到头来该不是养了几个苕货吧?”
“呸!你才是个苕货,我的娃儿个个都乖,你没发现他们都能哼上几句歌吗?”
“这有么子用,唱歌哪能讨得了饭吃。”
“这不一定,你看这世道变的多快,说不定哪天就能公开听邓丽君的歌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母亲常在深夜偷听“敌台。”
“敌台”在当时是禁止的,这是反革命的行为,反革命是要殊之灭之的。我姑父就因此坐过牢,我们家不能再有人坐牢了,况且父亲的回乡身份只能在处事中慎之又慎。父亲本是市里农校毕业,这在当时当地是了不得的学历,毕业后在城里工作,母亲当时也在城里工作。他们因音乐而结缘,婚后非常幸福。但那个年代不能拥有自己的小确幸,人人都要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就在这人整人的革命中,我父亲被小人陷害回了老家,母亲也随之跟了去。因我母亲爱好音乐,后在老家的小学当了一名音乐老师。在漫长而艰辛的生活中,弹奏脚风琴成了她的一大乐趣。
我常为母亲收听“敌台”而当心,但又很好奇,邓丽君唱的歌真有那么好听?以至于她甘愿冒如此风险?
我们家有一大一小两个收音机,大的放堂屋壁窗大家听,小的可随身携带。小收音机是父亲专程去城里买的,平常由母亲掌管,我与弟妹们谁成绩考的好,谁就可带着玩,这相当于现在还未出世的苹果8限量版那么拉风。为得到那宝贝,我无比卖力的听课做算术,成绩单一带回家就得到了收音机。但我的目的不是为拉风,就想听“敌台”里那个邓丽君。
那天正好父母都到姥姥家吃酒去了,眼看时机已到,天还没黑,我就哄弟妹们去睡觉。按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但他们偏不听我这猴子的话,哪肯乖乖睡觉,非要玩收音机听歌,没想到他们个个是音乐发烧友,革命歌曲边听边唱越唱越兴奋。《红星照我去战斗》《在希望的田野上》没完没了,直到我将台扭到另一个方向,所有人安静了下来。收音机里飘出柔情的女声《小城故事》《又见饮烟》一首接一首,我们全都着迷了。不知何时,门“咣”地一声,双亲大人回来了,没等我关机逃跑,耳光已上了身,不多不少,每人一记。我们家是严重的娇生惯养性,能吃上耳光证明事态严重!爸爸怒吼“任何人以后不准碰收音机!今天的事不准对任何人讲!”
母亲劝道“别太紧张了,没那么严重,政策在变,春天就要来了,别吓着孩子们。”从那以后,母亲开始教我们识简谱,学习音乐基础知识。并交给我一本厚厚的歌曲本,“你带他们几个小的学歌,年夜举行音乐会”。这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那天起,我们不再毫无节制地野了。我们几乎学会了当时所有流行的歌。母亲把脚风琴搬回家里,为我们伴奏排练。
村里人虽早已习惯了我们家的不正常,但时不时说些闲话。爷爷听到闲言碎语便跑到我家训斥:
“你们吃饱了撑的慌吧,没事做跟老子去田里挑菠菜到街上去卖!一个个都疯成什么样了!哪有这样过日子的!”
他的一通训斥引来邻里的哄堂大笑,我父亲连拥带推地把爷爷向门外挤,“您郎就别为我家操心了,我的娃我自己教,以后是猫是狗自己认。”这话其实也是说给村里人听的,意思是你们少管老子家闲事。
离大年三十越来越近,天气也越来越寒冷了,吹口气都能成冰。雪越积越厚,人们都不出门了,关在家吃腊鱼腊肉喝米酒,啃糍粑炒米麻糖,就如过冬的老鼠,屯足了食物,心安理得地等待年的到来。
大年三十,我与妹妹帮母亲准备年饭,弟弟们便帮父亲牵纸写对联、挂灯笼、拜祖宗烧钱纸。等一切就绪,父亲点燃了年饭的鞭炮,因为要开音乐会,我们的年饭要比别人家早。饭后,我们洗澡换新衣,父亲把火堆加了粗干柴,好让火烧的更旺,到处都点了蜡烛,使屋内显得无比亮堂。
音乐会的消息并未公开,但小伙伴们都带了板凳来我家。母亲调试好琴,向我示意。我按早拟好的节目单依次报单目,这算是我人生唯一的一次出彩做主持。
第一个节目是小妹的《采蘑菇的小姑娘》,紧接着小弟的《泥娃娃》,大弟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大妹的《马儿啊你慢些走》,我唱了《军港之夜色》《在希望的田野上》。随着节目的越来越精彩,人越聚越多,我还看到了我爷爷,他站在人群的最后面伸长了脖子。父亲将糖食果子、麻糖炒米、瓜子花生等摆满了八仙桌,还不时去添加,后又上了各种卤菜。人们毫不客气地边吃边看我们的演出。母亲的歌把音乐会推向高潮,她自弹自唱《南泥湾》《洪湖水浪打浪》,我听见最爱说我们家闲话的三幺姑也唱了起来,原来她也偷着学会了。最精彩的是我父亲的《花儿与少年》《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当他俩合唱《九九艳阳天》《红梅赞》《我的祖国》时,很多人跟着唱了起来,屋子里充满了掌声与叫好声。我第一次听到他们如此动听的歌声。这歌声,飘扬在平原的夜空,是那么嘹亮温暖。
曲尽人散,黑的夜被鹅毛大雪装点得缤纷柔和,那个年夜,我家的灯光在是那片平原里显得格外明亮,如夜空中最亮的星星。回头望见小弟与小妹躺在母亲的怀里,含笑进入了梦香,歌声定在他们的甜梦中回荡。这多么象十八世纪欧洲名画,母亲如画中的圣母,小弟与小妹正如那画中的天使。火光照耀在他们脸上,使他们无比明亮、温情、美丽。
《山居者》
雷琼,女,生于年2月,湖北省监利县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荆州日报》文学副刊编辑。著有文集《太阳花开》,小说、散文、诗歌散见于各报刊杂志。
凌晨四点,这是最不该受到打扰的时段。王小婧坐在车里,给周良发了一条小孩白癜风好不好治治疗白癜风的最好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