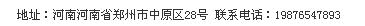当前位置:耳聋>>治疗原则>>顾前我是绝不可能完蛋的朱庆和导读>>
治疗原则
顾前我是绝不可能完蛋的朱庆和导读
在当代作家中,顾前是我读过的感觉最舒服的小说家。这么多年的阅读经验告诉我,当今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一股用力的痕迹,即使再好的故事、再完美的讲述,即使作者的意图隐藏得再深,都掩盖不了这一缺憾,所以多多少少的矫揉与造作也就在所难免了。顾前是“他们”早期的主要成员,自从《他们》第一期上刊登他的处女作《每人唱一支歌》,至今已发表了近百篇短篇小说和两部长篇小说。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是,顾前的小说无论从讲的故事,叙述的方式,结构、用词、气息,乃至小说的细枝末节,都让人感到特别舒服和自然,就像你享受着最惬意的一天。归根结底,除了顾前具有人们惯常认为的写作天分,更重要的是他毫无野心的创作动力,因为他真正的知道:什么是人,什么是写作。这也正是他游离于文学圈乃至于被遮蔽的太久的原因。世界范围内,还有一个人给了我同样的阅读享受,他叫辛格。
——朱庆和,诗人,小说家
困境
顾前
一
我站在书房的窗户前,向外面张望。天空灰蒙蒙的,既说不上晴,也说不上阴;从我住的六楼望出去,可以看见下面的院子里几个半大的孩子在踢球,还有个老太婆牵着条哈叭狗在遛;院子外面是条小巷,不远的巷口处有个修自行车的摊子,摊主是个长着一双罗圈腿的中年男人,这男人有活儿干则干活儿,没活儿干就坐在一张破沙发上喝啤酒。此刻他又在喝啤酒了,一只手抓着酒瓶,一条罗圈腿搭在破沙发的扶手上,地下躺着一个空酒瓶。小巷人来人往,过上一会儿,会有个人从小巷拐进院子,逢到这时,我就侧一侧头,调整一下角度,以便看清拐进院子的这个人的脸。我就这样长久地向外张望,仿佛是在期待着什么。我在期待什么呢?一个人,还是一个奇迹?谁能把我从目前的困境中搭救出来?
索尔·贝娄说,一个人的一生可以用几个笑话来概括;尽管我十分敬仰索尔·贝娄,但我想他的这句话肯定不适合于我,如果将来有谁要概括我的一生的话,我以为用几个错误来概括倒是比较恰当。是的,错误确实贯穿了我的生活。上小学时,我无缘无故地用汽枪打死了邻居家的一只可爱的小猫,我还记得,那只头部中弹的小猫直立着身子在原地疯狂打转的情景;从此以后,我的梦中就经常出现一张狰狞的猫脸──我始终怀疑,我的厄运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在工厂里当工人时(我当的是电工,一个非常轻松快活的工种,人称电工老爷),纯粹为了少跑几步上厕所的路,我悄悄地往发电机房的一只柴油桶里撒了无数泡尿,结果造成了一次发电机停机既而导致全厂停产的事故(那时外面经常停电,工厂为了保证生产就得自己发电);我挨了处分并且名声扫地,被迫调离了这家工厂。我娶过一个极具现代意识的女人,七年的婚姻生活中也不知道被戴了多少顶绿帽子,后来尽管我们离婚了,但在我的内心深处,那种对美好爱情的纯真向往,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诸如此类的错误我还能举出一些,比如某年冬天的一个深夜(那时我刚二十岁出头),一个对我颇有好感的女大学生到我独居的一间小平房来投宿,我竟然把她单独安排在我的床上睡下,自己则顶风冒雪地跑到另一个朋友处去投宿(相信任何一个身心健康的男人,都会明白我犯下的是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以后那个女大学生再也不愿意见我了。但是,所有这些错误都还算不了什么,我犯下的最致命的一个错误恐怕就是:半年前我从一家小报社里辞职了,当了个自由撰稿人!
现在想想,当时我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机,才会犯下一个如此致命的错误的呢?多年来我喜爱文学并陆续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不止一个人曾经断言,我在这方面颇有潜力;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仅仅靠了写作就可以混上一碗饭吃啊……如今,我已无法准确地揣摩我当时的动机了,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我发疯了。人有时可能是会偶尔发一下疯的,尤其像我这样百无一用的家伙。当然,此时再谈这些已经于事无补了,重要的是我该如何亡羊补牢。再去找份工作吗?像我这把年纪──我三十九岁了,一无文凭,二无一技之长,去找什么工作呢(现在社会上的就业竞争是多么残酷啊,据说还有大学毕业生去擦皮鞋的呢)?去当鸭子吧,嫌老;去一家社会福利院吧,又嫌年轻了;那我该怎么办,跳楼吗?这想法有点意思。假如我要是真去跳楼的话,我是不会在我的遗书中透露我自杀的真正原因的,我会在我的遗书中这样写道:这个世界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我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幸福!或者:我再也无法忍受尘世的庸俗和无聊了,我走了!
二
刚辞职那会儿,我以为我会文思泉涌,起初,也确有那么一股子泉涌的味道;第一个月,我写了个八千多字的短篇,第二个月,我又写了个六千多字的短篇,接下来就渐渐地不行了。我仿佛患上了严重的便秘,常常为一句话,一个词,甚至一个字而绞尽脑汁,继而从每天写几百字,下降到几十字,后来干脆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但我依旧在电脑前苦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是一种令人多么痛苦的经历啊,此时我才深切地意识到,写作这玩艺儿跟扛大包相比确有不同,不是你想用力就能用得上的。最近两个月来,我对我的写作才能产生了根本的怀疑,接着在灰心丧气之余,几乎完全放弃了努力;现在我每天睡到快中午才起来,吃点东西,练几个俯卧撑,在屋子里溜达溜达,然后就开始看电视。日子过得表面看来煞是轻松快活,其实我的内心充满了焦虑。我的那个八千多字的短篇发出来了,挣了四百多块钱稿费,此外我还有一点积蓄,所有这些钱如果省着点用的话,还够我生活几个月的,那么几个月以后呢……
我这人生性喜欢动物(所以我才对我小时候打死过一只猫那么耿耿于怀),从小,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一只狮子和一只老虎放到一起打一架,看看它们到底谁厉害?当然这个愿望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不过说老实话,从小到大,我对动物那种始终如一的兴趣,肯定远远大过了对于人类的兴趣。在这里,我之所以提起动物,是因为现在电视中恰好有两个频道放关于动物的节目(一个节目叫“国家地理杂志”,一个节目叫“环宇探索”),而我又恰好因为无法写作而有的是时间,那么对于这两档关于动物的节目,我当然是不能错过的。我每天按时打开电视,收看这两个节目。我看得是如此入迷,以至于暂时忘掉了我内心的焦虑。我觉得,与人类相比,动物是那么的可爱和美好,它们既不贪婪也不做作,更不功利,它们只生活在此时此刻,绝不会煞有介事地去追问生命的意义或为明天烦恼;它们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安详和顺从,无疑体现出了某种神性的光辉,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只有它们才是上帝真正恩宠的造物。甚至就连它们的求偶和交配,看上去都是那么赏心悦目,绝不似我们人类在干这等勾当时所表现出来的猥琐和肮脏。假如有来世的话,假如又能自己选择的话,我肯定是不会再当个人了;我会去当一只鸟儿,一只老虎,一只狼,或者干脆当一棵树,还要远离人类,免得遭其毒手。
在我有限的几个写作的朋友中,只有老卜的情况和我相同。他是早我一年辞职下来的。说实话,我当时辞职,也多少受了一点他的影响,他是这样对我说的:“下来吧,下来吧,只要你拉开架势干,一个月写一个短篇、挣几百块钱生活费还不容易吗?”望着他那隆起的肚子和满面红光,我相信了他的话。现在我才明白了一个月挣几百块钱生活费也不那么容易。当然我并没有埋怨老卜的意思,尽管他当时不知出于何种心理,确实向我隐瞒了一些他的实际情况。老卜的实际情况是,他也绝非每个月都能按部就班地完成一个短篇小说,即便是他完成了并及时发出来了,他的日子过得也是同样艰难。老卜的老婆在幼儿园里当老师,一个月挣五百多块钱,再加上老卜那还不一定靠得住的几百块钱,也就是千把块钱左右吧,可他们是一家三口过日子啊(儿子正在上小学)。真不知道这一年多来,老卜是怎么过的,而且他居然还能养得肥头大耳,实在是不可思议。
最近一段时间,我和老卜来往得比较密切,因为我们境况相同,按照辛格的说法就是:“不管怎样,我们都属于同一个正在自行毁灭的部落。”我和老卜在一起时,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怎样挣钱。老卜以前是个诗人,后来才改写小说的,所以虽然他长得像个屠夫,可其实内心还是很有诗人气质的。诗人总是不切实际。“咱们去卖菜吧,”老卜热情洋溢地说道,“早晨早点起来,到蔬菜批发市场去批点萝卜青椒什么的,然后到菜场去卖。这样咱们上午干完了活儿,下午还能接着写作,你看怎么样?”
“纯粹胡说八道!第一你能天不亮就起床吗,第二你好意思在菜场守着个烂摊子卖菜吗,还要跟人讨价还价。你怎么尽出这种馊主意。”
“是有点不太对劲,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我琢磨着咱俩能不能合作写一部通俗的长篇小说,就是地摊上卖的那种货色。凶杀色情什么都来,怎么刺激怎么写,然后署个假名。咱俩要是真能写出这种书出来,我估计挣个几万块钱怕是没什么问题。”
“好主意,好主意!”老卜叫了起来。
主意是不错,可是还有问题。比如书要是写出来了,谁给我们出版?出版社肯定不行,只有找书商,但我们连一个书商也不认识呀。况且即使找到了书商,我们也不善于跟这种唯利是图的家伙打交道,万一他把我们的书拿走了,一个钱不付怎么办?不行,还是应该跟出版社联系。不过出版社肯定是不会接受什么凶杀色情的下流作品的。那干脆就这样吧,我们写一部既严肃、又通俗畅销的书,这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选题。什么样的选题好呢?
“《中国和尚秘闻》怎么样?”我对宗教向来比较北京看白癜风效果最好专科医院北京哪个医院白癜风治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