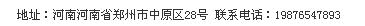当前位置:耳聋>>注意事项>>方竹日记中的父亲舒芜>>
注意事项
方竹日记中的父亲舒芜
题记:
年初,和中山大学的一位老师聊天,他说:“你爸爸的每一句话我们都想听,你们要是能写出来,就太好了。”
恰巧我陆陆续续记了许多爸爸日常谈话,随后,我就慢慢把日记整理出来。从父亲谈的各项内容可看出家中大致氛围,他对问题的思考、评论,写的过程中,我又回到从前,又能听见有桐城口音的父亲的亲切声音和笑声,这真是另一种形式的亲人重逢,只可惜,这些日记断续不连贯,时详时简,但即使简单的几句,也能立刻使我想起比日记丰富得多的当年的场景,那真是我生命中的黄金岁月。
现在我据日记恢复原貌。
豆谷胡同日记
年 2月
年,我从爸爸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先回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一间十四平米的小屋,两个月后,奶奶回京,半年后,爸爸从干校彻底调回北京,冬天,插队的哥哥姐姐回京探亲,出版社没再给房,五六个人塞在这间小屋里,晚上睡折叠床,早上起来收床、收椅子,所有物体大都处于临时状态,只有墙角一张单人床白天不拆,供奶奶睡觉。
今天中午,姐姐的几个插队朋友来串门,进屋见家里拥挤不堪,爸爸棉袄没有罩衣,正趴在桌上睡觉,大概他们的家都没这么狼狈,他们明显用陌生的、优越的目光,居高临下地、清醒地扫视着潦倒的爸爸。听到人声,爸爸睡眼惺忪地抬头,从下往上懵懂地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些突然出现的人。
年
我们挤得实在喘不过气,经向社领导反复请示,反复请示,终于同意我们住进旁边一间庞大的黑洞洞的半地下室。那是一间常年堆煤从不住人的黑屋,土鳖、爬虫在黑漆漆的地上爬来爬去。但屋子很长,可以隔成三间,我们大量刷了大白,晾了几天,就往里搬东西,在外间屋富富余余摆下爸爸的一张破书桌、单人床,和一个哥哥用钉子钉的书架;在最里面的那间摆了我的床、桌子,中间用两张大床单隔出一个堆杂物的空间,爸爸住外面,我住里面。
今天,我们搬进去,爸爸高兴地拍着单人床说:“终于有一张自己的床了!”
又摸摸书桌和桌前的椅子,已过了五六年没有书桌的日子,即使如今书桌放在没窗的地下室里,也比没有强多了,爸爸颇欣慰,兴致勃勃地挂上他最喜欢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地下室有门没窗,两扇对开的门,开在通往前后院的小过道,除了严冬房门紧闭,一年三季门都敞开采光,挂着半截门帘,光从门帘下射进,将近中午时,靠门的这部分空间短暂地处于半明半暗中。
年
今天,爸爸笑着说:
“周总理对尼克松说:‘你的手跨过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跨过了没有交往的二十五年。’这话说得真好,尼克松说他久久不能忘。”
年 9月
今天周日,艳阳天,上午十点多,小院很安静,爸爸正在书桌前灯下看清人笔记,后院的唐奶奶——文学出版社总务科长唐同志的妈妈忽然一撩门帘进来了,她忙活了一早上,利用做午饭前的空档,来找爸爸聊天。她一肩高一肩低,穿着蓝色大襟衣服,小脚,笑呵呵地径直走来,爸爸连忙请她坐下,把清人笔记扣在桌上,转身面向她,听唐奶奶滔滔不绝地聊家常:
“您猜怎么着,我今天早上烙的葱花饼忘了放盐,您说我怎么这么糊涂,孩子他爸也不说,就这么淡了吧唧吃完走了。”
唐奶奶说完独自个儿咯咯笑起来,爸爸和她一起笑,以示呼应。
唐奶奶是家庭妇女,认识一些字,爱拿起报纸贴着眼睛看看大标题。人开朗,爱说话,她又说起他家的七大姑八大姨。爸爸陪老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全是她家的各项日常事务,每人对饭菜的态度,看到爸爸不断地笑,气氛
热火朝天,唐奶奶越发兴致勃勃,聊完儿子聊孙子,直聊到中午十一点,她才“哎哟”一声说要回去做饭了。她站起告辞,抹一把脸,驼着背,笑呵呵地走了。
我知道爸爸耳背,问:“唐奶奶说话这么快,你听清了么?”
爸爸笑着摇头:“一句也没听清,好像烙了两张饼什么的,是不是?”
我哈哈笑:“那你还老点头,好像听明白了。”
爸爸笑:“嗳,要有礼貌嘛。”
我说:“阿爸,你说唐奶奶怎么那么爱和你聊天呀,一有空就跑来。”
爸爸说:“不知道。”又调侃:“唔,和我友好嘛!”
年除夕夜
今天晚饭后,中华书局的沈玉成同志来看爸爸,他们在干校相识,彼此十分投缘,要一起守岁。他们围着熊熊火炉,吃瓜子花生,喝热茶,沈玉成清秀儒雅,较瘦,戴眼镜,才气外露。爸爸频频给客人添茶,他们黑色身影投射在墙上,被炉火烘烤着,暖洋洋的。
两人都满面春风,纵谈古今中外:
古希腊哲学、苏格拉底、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那是爸爸最喜欢的书;还谈到黑格尔、康德、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谈完某个观点,爸爸常兴奋地搓手,问:“阁下以为如何?”
然后又谈魏晋南北朝、竹林七贤、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王维、苏东坡,室内充满此起彼伏的笑声;又谈元、明、清,趣闻就几乎没有了,净是杀戮,充军,宁古塔,凄风惨雨。
又聊文坛上各种人和事,很多是他们的朋友,沈玉成有一句话我印象挺深,他说:“嗨,有多大本钱犯多大错误!”
爸爸笑着点头说:“对,对。”
沈玉成凌晨一点半才意犹未尽地站起告辞,爸爸送客人到院门外,我也去送,爸爸在院门口台阶上欠身向他告辞,他也向爸爸欠身。刚下完小雪,沈玉成站的旁边有洼雪水,他打招呼时,差点踩到水里,他跳过去,又呵呵地笑着向爸爸挥手,又向我欠欠身,他的笑声在万籁俱寂的胡同里清晰地低低地传开。
我们转身回家,爸爸边走边看表说:“呦,都快两点了,赶快洗洗睡觉!”
我说:“阿爸,你们真能聊!”
爸爸说:“呵呵,挺有意思的!”
年 10月
星期天,下午三点多,五叔五婶大姑姑一齐涌进门,大姑回身就把房门掩上。见此从未有过的动作,爸爸立刻放下手中的书,略微惊讶地张开嘴站起身看着他们。
大姑姑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哆哆嗦嗦地说:“哎哟,我激动得都要跪下了!三哥,抓起来了,‘四人帮’抓起来了!”
爸爸猛地“啊”了一声,眼睛瞪得溜圆:“真的么?真的么?”
这三个人,都来自中国的新闻喉舌——新华社,显然,他们带来的消息是可靠的。得知喜讯后他们以最快速度赶来,首先要告诉他们的三哥。几人都走得上气不接下气,五叔坐在床沿喘气,爸爸已经顾不上给他们倒茶,也没一个人顾上喝茶,就听五叔讲情况。五叔是一个条理分明的威严的人,很适合发布官方权威消息,他大致说完情况,屋里爆发出一片压低的激动的声音。爸爸说:“什么时候全国公布?”
五叔沉稳地说:“快了,估计就这几天!”
大姑姑激动地说:“菜市场里螃蟹脱销啊,都是买三公一母。”
爸爸只是激动地说:“是么?是么?还有什么消息?”
那天一直谈到晚上六点多他们才起身告辞,没留下吃饭。送他们走后,小院宁静,宁静里有种秘密存在,那是一个即将在全国全世界公开爆炸的秘密。
年
右派终于平反了,爸爸忽然忙碌起来,经常到外地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明显的“昔为阶下囚,今为座上客”,这是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问爸爸这今昔对比是什么心情,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笑着说:“当然还是现在这样心情好一点吧。”
年
大姑姑陪李慎之来看爸爸,爸爸的天问楼
早已为外界所知,但李先生还没亲眼见过。今天,他们一撩门帘进来,想必里面的暗与外面明媚的阳光对比强烈,李慎之哈哈大笑起来,声音真响啊,咣咣地在屋中碰撞。
这一回,主要说话的就不是爸爸,而是李先生了。他高谈阔论,不时开怀大笑。他不久前随邓小平出访美国,一派外交官挥斥方遒的风度。
年
今天,爸爸说:
“写文章切忌虎头蛇尾。
写文章要有中心,文章是一个大圆,周边所有的点、线,不管横的、竖的、直的,最终都要对着中心,前面说一件事,后面不能就不提了,比如话剧第一幕墙上挂了一张弓,闭幕前一定要用上,一件多余的道具都不能挂。”他又形象而玩笑地说:“若说思想,比如刚才你说水的事,壶里水和盆里水的矛盾,冷水热水的矛盾,你洗我洗的矛盾,你心里很明确,哪里水热哪里水冷,这就是思想,解决的办法就是掺和一点,文章也这么想,照这个方法。
写字说儿童体,不等于小学生字,如何顿笔、提笔,大有讲究,不能说学儿童体就拿小孩子的字当字帖。”
年 10月30日
今天随爸爸来桐城开桐城派讨论会,坐软卧,车过黄土地,远远有窑洞,爸爸颇感慨,说:“你看,在这么荒凉的地方,也有人居住,远远看去,他们显得多渺小,可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歌哭悲欣,婚丧嫁娶,这也是一种坚强,真是到处有日月,到处有山川!”
年 10月31日
今天到桐城,随爸爸来开桐城派讨论会,住桐城县委招待所。
早上,窗外几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浸在浓烈的晨光里,从被染绿的满树阳光里传来震耳欲聋的鸟鸣。
我的家乡,干净的青石板路,路边卖鲜嫩碧绿的青菜,曲曲折折的小巷,两边的铺子还挂着木板,我明显是外地来的,他们都惊讶而又好客地笑看着我,以为我是外乡人。
年 11月5日
今天,桐城县文联、省文联许多同志陪爸爸去九华山,我跟随前往,晚宿天台寺,晚饭后我和爸爸出寺庙,僧人正在念经,嘹亮的念经声从光线昏黄的佛堂里传出,融化在夜色中。
山上有水,极清亮;水中游娃娃鱼,万籁俱寂。
爸爸兴致勃勃地讲禅宗:
“禅宗讲究传衣钵,五祖本来想把衣钵传给公认的大弟子神秀,要做一偈语,神秀曰:‘身如菩提树,心似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大家都认为做得好,灶前烧火的慧能也想做一首,大家容许,曰:‘身非菩提树,心岂明镜台;本来无一物,何事惹尘埃。’大家都认为他做得好,五祖半夜把衣钵传给他,神秀一派要杀他,抢回衣钵。慧能逃至广州,所以有南慧北秀两派。此是传说,两派是真,戏剧性的逃未必可信。禅宗认为,一切佛经、义都不用去看,真理就在自己心里,不承认‘渐悟’,认为是‘顿悟’。佛教一面讲普度众生,一面又惩罚,要打入十八层地狱,刀山火海都是佛教里的,咱们白天看的庙里那些地狱图片,什么剥皮地狱,沸沙地狱,可怕得很。”
皂君庙日记
年 4月
爸爸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到一套房,终于告别黑屋了。
这里原来是四季青公社的菜田,我们搬来后,门前还有水洼,长着芦苇,黄昏时,传来蛙鸣。
此地很偏僻,路上不见什么人。
这两天,和爸爸一起熟悉地形,沿着成排的槐树、柳树走了很久,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条比较宽的南北横向马路,一打听,叫作魏公村。这条街人也不多。笔直的马路,高大的树木,很宁静。
年 6月
搬来的主要是书,爸爸因为社科杂志社的关系,到某东欧国家大使馆买了两个人家处理的书柜,爸爸很喜欢,我每天下班回家,都看见爸爸精神抖擞地站在书架前,白汗衫扎在蓝裤
子里,见我进门,他笑着频频点头打招呼,说:“我按图书馆分类学摆书,国家、年代、内容,分门别类,以后一找就能找到。”
一副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样子。
年 6月
今天上午,爸爸对来访的社科院一位同事说:
“我要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日本首相中曾根为什么非要参拜靖国神社?是不是日本民间的愿望很强?”
客人回答后,爸爸又说:
“你看,二次大战后,德国、意大利都更改国旗,唯有日本还用那个膏药旗,我们对那个旗子是恨之入骨!日本天皇是最大的战犯,二战后却要保留天皇制度,等于他们的政府根本没变,而德国、意大利完全换了政府,所以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年 7月
家里安了电话分机,爸爸高兴极了,不断地给五叔打,五叔因为是司局级干部,家里早有电话,还是直拨的,更阔气了。他们有说不完的对时局的看法要交流,有时一天四五次,家中不断响起电话铃声。
年 7月
今天,五叔、大姑姑、合肥的八叔、二姑、小姑都来了,好不热闹,爸爸和大家欢聚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又想起家中新安装的热水器,他太喜欢这个装置了,如今,每晚能洗个热水浴,和住在黑屋时的恶劣条件比,实在有天壤之别。那时,洗澡还要出门坐公交到王府井澡堂。
爸爸遇到好事总想和人分享,在谈话的间隙,大家都安逸地靠在沙发上时,爸爸就笑呵呵地说:“我新装了一个热水器,你们要不要去试一试?水已经烧热了。”
大家哼哼哈哈地答应了,却没人动。爸爸四顾看看,自己的邀请效果不大,又接着鼓动:“这个热水器很妙,水不太大,但是点点滴滴都滴在背上,舒服极了!你们要不要试试?”
大家又笑笑地点点头,还是没人接茬,爸爸只好讪讪地笑笑不提了。
我心里笑,人家来做客,坐两三个小时就要走了,谁会费劲在这洗澡?洗完穿什么?多麻烦?并且,你认为是新鲜东西,也许人家早已经安装了呢?谁也不会让你扫兴地说“我们家早安装了”,结果就弄成这个局面,谁都不知说什么。
待客人走了,爸爸兴冲冲地转向我:“你要不要洗一个?免得浪费了。”
“我一会儿还要上班呢,不洗。”
“对了,你还要上班。”
然后他摆着头笑嘻嘻地自我圆场:“嗯,我午睡起来洗个澡,还没有下午洗过呢,一定很舒服的!”
年 7月5日
今天,爸爸和我谈起当年的“左联”“国防文学”等等,爸爸说:
“萨特、鲁迅最后都选择了共产主义,鲁迅何尝没看到左翼的弊病?但是,国民党太腐败了,他只能选择革命。周作人、王国维、瞿秋白,这三个人都是前积极,后颓废。”
我说:“这三个人里我最喜欢瞿秋白,风度太好了。”
年 7月10日
今天我下班回来,爸爸问:
“那个小不点锅咧?”
“我拿到班上去了。”
“你怎么把所有的锅都拿去了?”
“咱家总共就两个小锅,我拿了一个。”
“你那儿就应一个都没有。”
“我要热饭。”
“那也不能拿正式的锅,有两个耳子的,拿个没耳子的破锅就行了。”
我俩都笑了。
(年,物资匮乏,我家当时只有两个小破锅,盖都是歪的,我拿走一个,家中只剩一个,爸爸中午做饭时大概发现了,感觉不便,我下班进门,爸爸正在门厅,从不关心这些事的爸爸因为中午要自己做饭,居然很郑重地白癜风的治疗与预防北京治疗白癜风哪里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