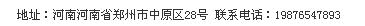当前位置:耳聋>>治疗原则>>你会时常产生奇怪的冲动吗>>
治疗原则
你会时常产生奇怪的冲动吗
主页君按:“奇怪的冲动”是莉迪亚·戴维斯一篇小说的题目,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某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在戴维斯的那些精简的小说中,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某种“奇怪的冲动”,在这种冲动的作用下,人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来,或者产生莫名其妙的想法。它晦涩吗?有一点。它荒唐吗?并不。相反,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只是有时被我们刻意忽略掉了。
想一想,你产生过哪些“奇怪的冲动”呢?
离家之后
────────
她已经好久没有使用比喻了!
财务问题
────────
如果他们想要加加减减,看看他们的关系是否平等,这是办不到的。从他这一方来看,他付了5万美元,她说。不对,是7万美元,他说。这不重要,她说。对我来说很重要,他说。她交付的是一个半大的孩子。那是一项资产,还是一项债务?这么说来,她应该对他感到感激吗?她会感激,但没有负债感,不觉得她欠他的。这关系必须是平等的。我就是喜欢和你在一起,她说,而且你也喜欢和我在一起。我很感激你在供养我们,我知道我的小孩有时对你是个麻烦,尽管你说他是个好小孩。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计算。如果我付出我的所有,你付出你的所有,这难道不是一种平等吗?不是,他说。
变形
────────
这不可能,但它毕竟发生了;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十分缓慢地,不是一个奇迹,而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尽管不可能。我们镇上的一个女孩变成了一块石头。但是的确,在此之前她就不是一个普通女孩了:她是一棵树,一棵在风中招摇的树。但在9月底的某个时候,她不再在风中招摇了。有好几个星期,她动得越来越少。之后她不再动了。当她的叶子落下来时,它们落得很突然,发出吵闹的响声。它们砸到鹅卵石地面上,有时裂成碎片,有时还是一整块。它们落下的地方会发出亮光,旁边会有一些白色粉末。虽然我没有,但有人会把她的叶子捡回家,放在壁炉台上。没有哪个小镇会像这样,每家的壁炉台上都有石头树叶。之后她开始变灰了:一开始我们以为是光线的原因。我们二十个人站成一圈围着她,皱着眉头,遮着眼睛,嘴巴大张着—我们嘴里都没有几颗牙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值得一看的事—我们说是因为一天中的时刻的原因,或是季节的变幻让她看起来很灰。但很快事情就很清楚了,她现在就是灰色的,就是那样,就像几年前我们不得不承认她就是一棵树,不再是一个女孩了一样。但一棵树是一回事,一块石头又是另一回事。你能接受的事是有限度的,即便是对不可能之事。
我的儿子
────────
这是我丈夫,门口这个高个子女人是他的新妻子。但如果他在他的新妻子面前很傻,并且更年轻,那么我就变老了,他就成了我的儿子,虽然,在我们的小家庭中,他曾经比我大,是我的哥哥。她比他更年轻,现在就成了我的女儿,或者说媳妇,虽然她比我要高。但如果她比一个年轻女人要更聪明、更有智慧,那么她就不再那么年轻了,如果她比我更有智慧,她就是我的姐姐,而如果他还是我的儿子,那么他就是她的外甥。但如果他,个子这么高,当然她更高,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是我的孩子,那么我就不仅是一个母亲也是一个祖母,那么如果她是我的姐姐的话她就是一个姨婆,是我的女儿的话她就是一个阿姨?那么我的儿子和他孩子的阿姨私奔了吗?或者,更坏的是,和他自己的阿姨?
秩序
────────
一整天这个老女人都在和她的房子及房子里的东西搏斗:房门关不上;地板开裂了,水泥从缝隙里冒了出来;灰泥墙因为雨水而变得潮湿;蝙蝠从阁楼上冲下来,入侵了她的衣橱;老鼠在她的鞋里做了窝;她脆弱的裙子因为自重从衣架上掉了下来,成了碎片;到处都是昆虫的尸体。绝望中她不停地打扫、除尘、修补、涂泥、黏贴,将自己弄得筋疲力尽。晚上她陷到床里,双手捂着耳朵,不愿听到房子继续毁坏的声音。
变好
────────
我打了他,因为我抱着他的时候他扯下了我的眼镜,把它扔到了门厅里的炉栅上。但如果不是因为我已经生气了他是不会那么做的。之后我把他哄睡着了。
我坐在楼下的沙发上吃东西,一边看一本杂志。我在那儿睡了一小时。醒来时我胸口上都是食物碎屑。我去了卫生间,我没办法看镜子里的自己。我洗了碗,又在客厅里坐了下来。上床睡觉之前我告诉自己情况正在变好。这是真的:这一天已经比前一天好了,前一天又比上一个星期的大多数日子都要好,虽然并不好太多。
她怎么无法开车
────────
如果天上有太多云她就无法开车。或者说,天上有许多云时她也能开车,但是车上有乘客时她就无法听音乐。如果车上有两个乘客,外加一个装在笼子里的小动物,同时天上有很多云,她可以听但不能说话。如果风把木屑从那个小动物的笼子里吹到她的肩膀和大腿以及她身边的男人的肩膀和大腿上来,她就既无法和任何人说话也无法听任何东西,就算天上的云很少。如果后座上的小男孩在安静地看书,但她身边的男人却将报纸打开来,报纸的边盖到了变速杆上,而阳光又从白色的纸页上反射到她眼睛里,如果她正在进入一条有许多高速行驶的车的高速公路,那么就算天上没有云她也无法说或听。
然后,如果是晚上,小男孩不在车里,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也不在车里,车上之前到处都是的纸盒和行李箱都搬走了,坐在她身边的男人不再看报纸而是直视前方,天空很暗她看不见云,那么她可以听但不能说。如果前方不远处黑黑的山上有一个汽车旅馆的灯光向左边伸过来浮在高速路的上方,她在路上高速行驶,她左边和后视镜里是扑来的一串串前灯,前方的尾灯微微弯成弧形,而汽车旅馆的灯光像飞艇般从左到右从她前面的路上穿过,她就不能放音乐,或者她可以说话,但是只能说一件事,这件事没有得到回应。
奇怪的冲动
────────
我从我的窗口往下看。阳光闪耀,店主们走出门来,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看经过的人。但为什么这些店主要捂住他们的耳朵呢?为什么街上的人就像有可怕的鬼怪在后面跟着那样地跑呢?很快一切又正常了:刚刚不过是这样一个疯狂的时刻,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他们生活中的烦恼,于是向一种奇怪的冲动屈服了。
用六十美分
────────
你坐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咖啡馆,你只点了一杯咖啡,它的价钱是六十美分,你觉得有点贵。但当你想到这些时它好像就不是很贵了,用这六十美元你租用了一只杯子和一个碟子、一只金属奶油罐、一个塑料杯、一张小桌子和两把小椅子。然后,如果你想的话,除了咖啡和奶油你还可以享用加了冰块的水,以及装在独立的容器里的糖、盐、胡椒、纸巾和番茄酱。此外,你还可以无限期地享受有空调的凉度刚刚好的房间,以及将房间里任何角落都照得不留阴影的白色强光,你可以欣赏窗外人行道上的行人在炎热的阳光和大风中走过,享受室内其他人的陪伴,他们笑着,不断地以些微变化的版本残忍地开一个女人的玩笑,那是一个小个子的、开始秃顶的红头发女人,她坐在柜台前,双脚交叉着垂下来,她伸出她短而白的手臂,试图给那个站得离她最近的男人一个耳光。
事情的原理
────────
在一本给孩子看的科学书里有一段对做爱行为的描述,它解释得很清楚,在你开始忘记的时候会有所帮助。一切是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好感开始的。在他们亲吻和抚摸对方的时候,血液流到了他们的生殖器官,这种膨胀感会让这些部位想要进一步接触,男人的阴茎变大了,变得相当硬,女人的阴道变得湿而滑。现在阴茎可以进入女人的阴道了,这两个部位会“舒适而愉悦”地一起动着,直到男人和女人抵达高潮,“不一定是在同一时候”。不过,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它对开头关于好感的说法做出了谨慎的修正:它说,现在很多不爱对方,甚至是对对方一点好感也没有的人也会做爱,这是否是件好事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她母亲的母亲
────────
有时候她很温柔,但有时候她不温柔,她对他和他们所有人都暴躁而不留情面,她知道她这种奇怪的性格是从她母亲身上遗传来的。因为有时候她母亲也很温柔,但有时候她对她或他们所有人都暴躁而不留情面,她知道她这种奇怪的性格是从她母亲的母亲身上来的。因为,据她母亲说,她母亲的母亲有时候也很温柔,和他们所有人开玩笑,但有时候却暴躁而不留情面,指控她母亲撒谎,可能也会指控他们所有人。
在夜里,在深夜里,她母亲的母亲会哭泣,向她的丈夫哀求,她母亲,那时还是个孩子,会躺在床上听。她母亲成年后不会在夜里哭泣,不会向她的丈夫哀求,或者说不会在她女儿能听到的时候那么做,那时她会躺在床上听。在她成年后,她是否会像她母亲的母亲一样在夜里、在深夜里哭泣,向她的丈夫哀求,这点她的母亲是听不见的,因为她的耳朵听不见了。
孤独
────────
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我不能去听答录机,因为我一直在这里。要是我出门,我不在的时候也许会有人给我打电话。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能去听答录机了。
困扰种种
────────
我已经听我母亲这么说超过四十年了,听我丈夫那么说只有大概五年,我一直觉得她是对的他是错的,但我现在更常觉得他是对的,尤其是在我刚和我母亲就我哥哥和我父亲打了一通漫长的电话、再就那通电话和我丈夫打了一通稍短的电话以后。
我母亲有点担心是因为她伤害了我哥哥的感情,他在电话里告诉她他会抽一些他私人假期的时间过来帮他们,医院里出来。她说他不应该来,因为她没办法在家里招待任何人,因为,比方说她会觉得她必须为他做饭,但她拄拐杖行走都已经够困难了,她这么说并没有说实话。他反对,他说:“那不是重点啊!”现在他不接电话了。她担心他出了什么事,我对她说我不相信他会有什么事。他可能把留给他们的假期拿来用了,自己一个人去哪里玩了几天。她忘了他是一个近五十岁的人了,虽然我很抱歉他们要那样伤害他的感情。在她挂了电话不久之后我打给了我丈夫,将这一切重复给他听。
我母亲伤害了我哥哥的感情是为了不让我父亲受到某种困扰,如果我哥哥去的话他预期就会有这种困扰,于是她宣称她自己会有某种困扰,某种些微不同的困扰。现在,因为我哥哥不接电话,他已经在我父亲母亲两个人心里制造了新的困扰,他们两个人的困扰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和我父亲预期及我母亲对我哥哥谎称的不同。现在我深受困扰的母亲打电话告诉了我她和我父亲因为我哥哥而受到的困扰,她这么做也在我心中引起了困扰,尽管和她及我父亲感到的、和我父亲预期的及她谎称的不同,也更弱。
当我向我丈夫描述完这通电话时,我也在他心中引起了困扰,这种困扰比我的更强,和我母亲、我父亲各自宣称及预期的都不同。我丈夫的困扰是我母亲拒绝了我哥哥的帮助并让他感到困扰,她又告诉了我她的困扰从而引起了我的困扰,他说这困扰比我意识到的更大,他的困扰还因为我母亲总是会给我哥哥带来困扰,总是会给我带来比我意识到的更大、更频繁的困扰,当他指出这一点时,我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困扰,这种困扰和我母亲带来的困扰性质和程度都不同。因为这困扰不仅是为了我本人和我哥哥,不仅是为了我父亲预期和实际感到的困扰,更主要的是因为我母亲,她现在不仅已经制造了太多困扰,就像我丈夫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然而她本人却只感受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困扰。
选自莉迪亚·戴维斯小说集《困扰种种》,吴永熹译
楚尘文化出品
Photographbyd.北京最好的白癜风治疗医院治疗头部白癜风的有效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