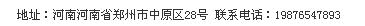当前位置:耳聋>>治疗方案>>马晓康醉话酒魂致高世现先生的一>>
治疗方案
马晓康醉话酒魂致高世现先生的一
醉话《酒魂》
——致高世现先生
马晓康
轮回Vol.01壹/
高先生,我15岁失去家庭,22岁又重新拥有它。7年的空白,没有阅读,很少有朋友,一切却都与诗有关。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它给了我看世界的独特视角。
(之前喝醉后给您写的三千多字我决定作废,传统式的评论,太单调,虽然能表达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但那不是我想要的状态。我希望能寻找一个冷静的方式来书写,狂暴的冷静,我可以冷冷地看周围的一切,但胯下必须是我心中的野兽。时隔一年,我渐渐熟悉了冷静地控制自己,当然,还不是很熟练,但比以前要好多了。再引用一句古人的客套话——“作此拙文,仅供一笑。”)
在凡人的世界里,人们千方百计地钻研着如何好好活着,这使人生变得肿胀,也让他们慢慢害怕自由地活动。尽管那些在规定秩序内的阳光总能照耀出一些鲜花,我们也无法抵挡地对其产生爱慕。可是,鲜花背后不仅有猛兽的威胁,还有更多看不见的腐烂。
(一直活在阳光照耀下,眼睛照久了,会有盲区。)
总有人要去坚守于“活着”之外,在一切走向衰弱的秋天,大多善良性的生命都要变成被收获的果实了,所以,我想把这篇拖了近一年的文章和落叶的命运,一起做个完结。其实,一年时间并不算长,如果评价一个人的精神史,却没有另一人的精神史去对话,那将是多么孤独和羞耻的事。(我曾因年轻和野心产生过无数急功近利的想法,为此我后悔不已,哪怕没有听众去理解这种后悔,可我知道它存在着,这就够了!)
上来就谈诗,是很俗的,俗不可耐。诗不会因为不谈而断绝,也不会因为谈而走向鼎盛,诗,只属于少数人。每个人的思想维度都不同,从头到尾地品头论足,其实挺吓人的,就像一个男人大谈女人生孩子的感受一样,太恐怖了。
“割股相下酒,谈笑鬼神惊。”在墨侠血性几近销声匿迹的今天,武器和骨头变得越来越陌生,压在我们头上的种种“责任”,早已碎裂了我们“割股”的勇气。推心置腹的精神自裁(既自省)也成了一件贵族化的事,而这是我正在做和希望完成的。
(常青树没什么意思,那些熬到皑皑白雪还挺着死枝子,挂着几片黄树叶的,才是真壮士。)
年7月到9月,《酒魂》,除却封面、目录和版权页,我从头到尾读了三遍,还抄了一遍笔记。这期间我去过武汉和杭州,江南小景并没有带给我多少启发。在杭州夜市里,怀揣《酒魂》如在衣服里塞了一团烈火,江南的雅气不等近身就被烧尽了。到了年,又偶尔翻出来看了几次,生怕自己忘了。翻看,也只挑自己最安静的时候,写长诗是一个拼气和加速燃烧自己的过程,读长诗,是从内而外地将自己烘干,必须静下来才能看懂。
静下来,很重要,却很难。这不是几天能做到的,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和心力。可我又不是个聪明人,生怕写跑题,毕竟“内心”这个笼子已被我用来关押我的野兽,再也没有空间来关押自己了。就像人们越来越复杂的情绪,它们在城市里迷路、在乡村里迷路、在某个国家迷路、在地球上迷路,不停地寄生,是它们唯一的活路。
我喜欢大醉,哪怕乱说话也没事,头疼多了会上瘾,半醒间能狠狠地踢几脚鬼门关前的石头。
我说,《酒魂》是一座诗歌长城,这肯定会遭人反驳。可长城就在那儿,不管你说它宏伟不宏伟,它都在。你可以无知地用一栋30平米的精装小公寓去和长城比时尚,也可以用秋风茅草屋去和长城比凄凉,但这都伤害不到长城本身。至于长城沿途生长过什么样的花草或城市,更不必在意,那仅仅是时代的附加品,长城在,它们就一定会在。
但凡过于宏大的建筑,我都喜欢走进去,抚摸每一块砖石,享受它传递给我的故事。
不过,我并不在意这首诗的结构承接和形式,如同没人会在意长城的最初设计图纸一样。结构,是可以被画出来,假使一个人的精神图腾可以被画出来,像设计图纸一样被标出零件位置……我无法想象出比这更可怕或更虚伪的事。
可人的精神、情感,又是什么?我们从母体获得营养,成人形,母亲却永远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就连一起出生的双胞胎都不会知道对方的心思。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宇宙,像王一样,主宰着那里的臣民。
土地,人类最初的本源,诞生于在水火之间。我们的谷物也是从土地里长大,而我们正在做的事却是在背叛土地。您在祭辞里写道,“水为母,火为父,/五粮的精液,时间的幼儿。”无论是《圣经》还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女娲”,他俩都没有经过谁同意,便将我们的祖先从土地里拽了出来。
不妨把他们拼到一起看。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蛊惑而食用了禁果,注定了人会屈服于欲望的诱惑。诗人或许是那堕落瞬间的人吧,既保留了神性又被欲望所操纵,真令人头疼。连女娲都不耐烦了,补天那么大的工程不嫌累,造人的时候却干脆甩起了泥巴点……
做一粒尘土,比做人好得多。尘土没那么多限制,有风就可以飞起来,没风也可以安静到最低处。人却只是泥巴,沾了水,埵在哪里都是一滩烂泥。唯有被火烤透了,这湿淋淋的母爱,干巴皱裂的人,才真正算是独立了。
“火父水母”一说也被应用于茶道中,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品尝悟人生的道理吧。如果不写到这里,我也不知道自己从前喝茶是为了悟什么,可能仅仅是为了解渴。
(这得感谢您的诗。)
高先生,《酒魂》的开场,让我想到了蛮荒黄土上,一群跪向太阳朝拜的黑影子。酒,是粮食的意外,重新联通了“神”、土地和人的联系。我想,这种精神应该类似于人回归母体,寻找最本初的纯洁一样吧。
日月构成我们阴阳的雏形,酒打通了我们通往两极的通道。这还不够,“酒”是个习惯送佛送到西的家伙,不是吗?无家可归的诗人都会被酒驮进自己的归宿,就像封神台上封神,终会有自己的位置。
可阴阳是轮回,所以日月轮回,诗人的肝肠寸断也是轮回,酒里来酒里去的归宿,也是轮回。
土里来的我们,死后也回到土里去……
天边传来一句诗——“驾着轮回的马车我又回来了/只有诗歌,迎我”。
煮酒Vol.02贰/
诗人难以享受凡人的欢愉,哪怕是亲情、友情,在追寻诗的路上,总是背负着残缺而闪光的部分。这欢愉像大地上五彩斑斓的鲜花,也像奔腾不息的流水、瀑布,一切美好而富有生命力的事物,我们爱并倾慕着。
可属于诗人的那一朵花,人们仅仅知道它是一朵花,却从未在万花丛中见过。我们能闻到它散发的独特的香气,偶尔也能摸到它花瓣的轮廓,可它却是个调皮的精灵,一瞬即逝。
暴雨中,所有花都会被打湿,只有属于诗的那一朵还挺着,再来狂风也好,都改变不了它分毫,任凭天上的闪电怒视大地,在它的基因里,没有屈服。
可诗人也是人,更是泥土,暴雨和狂风会毫不留情地摧垮我们。
高先生,万花丛中,沾满花香也好,鞋子踩满了泥土也罢。那些真正的诗人终会在花丛里倒下,就像我们现在的文本在语言前牺牲一样。牺牲的文本,是诗的土壤。诗人的尸体,则是诗的种子。
高先生。诗,是我们唯一可以还魂的附体。在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倒在万花丛中的姿势之前,你一定也会觉得有愧于家庭云云。我已说过,这是诗人逃不开的宿命,我们注定无法去享受这些欢愉。例如玫瑰,这平原、山地和邻居花圃里的座上宾,或许会在沙漠中落魄成一株仙人掌。它会变得更尖锐,却忘记了自身的高贵。我们忘记梦里的自己可以飞翔,也是这么回事,只是现实与梦,没有沙漠和草地那么大的区别而已。
酒,是防止我们遗忘灵性的良药。在酒的陷阱里踩空,也是每个诗人都付出过的代价。
“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长安醉生梦死的人一定在嘲笑李白的无能吧!却不知李白的笑声已传到数百年外,可惜他们那一双短耳朵,只听到天姥山上无奈的叹息,却再也不能亲历历史长河中的回声了。
忧愤出诗人,诗人的基因里有对抗世界的抗体,也有逼着自己一遍遍去接纳世界的先天习性。是的,就是这个被篡改了一遍又一遍的世界。
说谎的历史,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如同一份被修改完整,却永远被拒绝审批的稿件。无奈,诗人又要用尽力气,在说谎的历史中不太说谎的部分里,为自己的名字投票。这无疑让我们分裂,您说您有三个灵魂,第一个灵魂用内心的残缺来酿酒,第二个灵魂去写下所有愤怒以保持洁白,第三个灵魂忍辱负重地记录所有。
用一辈子的文本尸体去换史书页码上的一页简介?高先生,这一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留名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想在史书上狠狠地折一个角,折过一次,就永远都被折过,无法被投机者的笔头篡改……
“一定会有一个折角,仅仅为我而标记,疯狂的中国将我伤害成诗”这才是您安放三个灵魂的归宿吧。
高先生。从古代穿越到现代,没有一个真正的诗人会去出卖诗的。您是否也看到了,花丛中,那些披着诗人斗篷的掘金者。诗人手里的镰刀,是用来割诗的,也许一辈子都寻不到。能劈向虚无的镰刀,诗人的镰刀,却在艳花的妖娆前无可奈何。
花可以被挖出来,栽进自家瓦盆里,屈服为私有财产。可诗不会,再多自欺欺人的话都不会。找一株假花来指鹿为马更是可笑。诗是如此挑剔,不会去选择贫瘠的土壤,深入地心的根需要深厚的土壤。写长诗,眼看着万花丛的花一点点被掘金者挖走,这需要多大的忍耐!
好在中国的诗人并不寂寞,不必向配索阿那样为自己创造异名者。屈原、陶渊明、骆宾王、杜甫、李贺、苏轼等等,在迷失或困境中,都能与我们对话。或颠沛流离或清贫豁达或大起大落的一生,故人们活得多么坦荡,任凭我们轻薄地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从不辩驳和解释。牺牲的文本,可以生火,照暖百年后的人,却温不热世间的奇寒。
青梅煮酒可以论天下英雄,投诗煮酒可以借酒还魂。
在大雨连绵的时候,我们只好借古人的火来点燃自己。
呵呵。那些习惯了在雨天抱怨伞不好用的人,习惯了顺从乌云。
“老朽们!盛世是这般的么”
对抗Vol.03叁/
对一个文人来说,最悲壮的模样莫过于披头散发的醉态。披头散发、一袭白衣、醉步于山道间,饮却一半的酒壶叮咚作响。身后,山高水长,大雾遮蔽下的苍翠时隐时现,或是夕阳下从一片残旧蓑衣的背后飞出几只寒鸦。
头垂得越低,那云雾就聚集得越密。起身,拂袖,举起酒壶痛饮,几滴酒沿着胡须滴进地面,一切障眼之物散尽,或苍黄或清秀,寰宇被一口酒呛得团团转。
这是断肠人的天涯,每个人都在传诵“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可没有几个人真正去过那里,去往“天涯”的门票太贵了,搞不好就要搭上一辈子。
可我又不得不想到李白,落寞的情景一旦在脑海里形成,古人们其实都活成了一体,真的没必要去区分姓甚名谁了……
可惜!“再快的鼓点也唤不住,跌坠下来的/半盏大唐的江山”
高先生,我坚信,任何对历史没有幻想的诗人都是可疑的。历史,是镜子里的昨日,永远让我们唏嘘,却无法抵达,可在我们寻找通往历史的过程中,却离肉体存在的世界越来越远。正如您所写的“那个我去不了的世界,却无比接近/而这个困我其中的人间却无比遥远/必然它是祖宗的疮痍,必然是它十八代的重复”。
这是诗人的困境,除了诗艺的语言困境,还有人类的“语言”困境。一切被“语言”架构起来的,都像注水猪肉,我们被嘴里所说的语言控制了风俗习惯,甚至控制了我们的思维。相比电脑,我们更像活在数码世界却不自知的一堆数据,只是造物者给了我们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可悲,这空间也是被数据编程过且封闭的。“语言”给我们的框架,望不到边际。
高先生。在困境中徘徊的诗人,像流浪者,虚幻的月光是我们的全部财产。不是吗?在您的诗中,您和李白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而“房租可以在月光那里抵扣”。无论是夜里山涧舞剑高歌的白衣隐者,还是披着黑色麻斗篷怀揣十字架在银色大地上逃亡的教士,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追求永恒和完整,更是为了保护自身对这个世界发声的方式……
诗人,融入情感的每一首诗,也是一种发声方式……
“我是每天搬一块身体进去,支离破碎的器官/等音响组成那一天我就可以放手了/因为到了那一天,我的歌/已足够支付永恒的费用,还有什么不可以宽恕?”
尽管如此,我们的月亮只有一个,“李白的月亮也只有一个”。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诗人所有的通灵感才能完全调动起来,虽然一些评论家称其为“超然感”。可这只有诗人与诗人之间才能感受到,不是寥寥几百字的吹捧可以替代的……
(高先生。这通灵感,可以仅仅是一阵风或树叶的一颤,可以是我们仰望星空时的一个激灵。梦中故人的饥寒、无奈、热血和坦荡,都会袭来,袭遍全身。这些感觉将住进身体,你将代替它千百年前的主人保管它。那些被我们误解误读的,也会因此而被赋予生命力,它们是真实存在的,最美丽的错误,让我们拥有无数个地域,甚至千百个相同的土地上各自被千百个臆想占据。)
内向的肉体里住着一个风流的精神主义者。诗人是情种,爱情、友情、亲情,敏感又迟钝大意,一切寄托了情的事物都可以成为情人、兄弟和亲人。风、雨、雷电或树木,甚至是一个坟头,短暂的记忆就留在那儿,分开后彼此在极远方等待对方,再也不相见。
黑夜里探路的人,难以与月亮达成和解。向黑前行,注定收不到脑后传来的信。高先生,这是一条何其孤绝的路呢。一遍又一遍在脑海中重演历史,重演想象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可以回到唐朝也可以回到民国。所谓精神之旅,何尝不是诗人无奈的自我放逐呢?
“这么多年是我无身的头在奔跑,在人的止境/我无头之躯,就不用顾形象了/身我——头我——我就有了元我与辅我/以身我的方式静待头我的大完成/现在的情形是,身我是一颗宇宙之树,头我是太阳//去吧,去开门。我要去迎接更神秘的我进来”可开门之后又会是什么呢?继续无止境地奔跑,在黑暗中游泳,所有被前人们拨开的浓雾,会在我们过后再次聚拢,所有在我们前方被透视的,又再一次被浓雾所淹没。
“文字,是我胸中的兵器,我胸仿似古老兵器工厂”。
只是,这兵器,只能伤害诗人自己。心中多少忧患也敌不过经济时代酒桌上的推杯换盏,一瓶茅台就让醉倒了他们心中的半壁江山,那个叫“原则”的城墙,不过是扇随时可以打开的门而已……
可我们听得见,从更不可及的黑暗中传来的宴乐、碰杯声……
在这个时代,诗人的死,被人从悲怆演化为一种浪漫象征,继而成为商业活动中一枚“可用的符号”。另一个世界的人多么伟大,总会迎来许多人的缅怀。哪怕是默默无名的诗人死去,也会被人狠狠地利用一把。悲哀啊!高先生,死人的事,本不和我们这些活人相干,可骨气和心中的血是热的,闭口不言,像含着一块热山芋,还要承受那些早已吐出山芋并嘲笑你的冷言冷语。
呵呵,对此,我有什么好感慨的呢。总有一些时代要葬送在宴席上,总有一些诗人要以死来记录一代人崩溃的开端。我们既不愿同流合污,也没有做好与死神饮酒的准备,放逐路上还有许多事要做,要继续对抗下去!我很喜欢简明先生的《对手》一诗,诗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抗的结果,只是这结果无关胜负。
可挫败感和成就感总是并行的。冷静与年轻的野心和肉体作对,囚禁自己的房间与窗外的车水马龙作对,就像一滴异化了的雨水,悬挂在半空里,不知道究竟该落下还是继续旅行。落地,一切就能结束,不甘心乌云的污浊却也舍不得接下来的风景……
高先生,您是否也有过这种无力感呢?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淫者留其名。”
敌意Vol.04肆/
高先生,我不是个悲观主义者,更不是顾影自怜的人,但我坚信着,每个日子都充满了敌意。我特别害怕那些积极向上的人,你大可以在一日里积极地去做每一件事。你可以口口声声地说,今天活得值了。可时间已经夺走了你的一天,人活着只是在寻找适合自己的死法。
再次强调,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只是讨厌遮掩,只是痴迷于揭开赤裸裸真相后的血腥味。那些所有让他们闭口不提,装聋作哑的事,我都喜欢……
尽管我写诗时间不长,但我相信一个人的精神是无法用写诗时间长短来衡量的。有人写了几十年仍是个名利之徒,靠一点自己本不相信却要假装相信的浮夸来支撑自己,他们生活无忧,却像一个捡了一张电影门票票根却对每个人都说自己看了一场电影的穷孩子,真是可怜。
“我在长诗中流亡了多少年,见过囚牛、嘲讽、蒲牢、狻猊、\赑屃、狴犴、螭吻、椒图、蚣蝮,却从未见过不装聋装哑装瞎的人”
这是您的诗,这也是我们所默契的地方,高先生。
诗,甚至一切文本,都是和语言战斗过后的尸体。尸体之上,作者的精神得以永生,无论是丑陋的还是高尚的,几年或几十年后就被扫进尘堆里遗忘的,或准备在数百年千年后发光的,都在那里安静地睡着。
高先生,这在中国的语境里是不该出现的话。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忠实自己的内心,将它说出来——“我们都是在寻找适合自己死法的人,长诗,是为了给自己留一个更宽的坟墓,只有在那里才能得到安宁吧”。可只要还有一日活着,放逐就仍在继续……
“我是历史的孤儿,我那么古老熟悉如乡土/与时俱进的眼泪却如废墟。/我爱什么,我又恨什么,/深沉的目光像施肥的老农,焦急的/眉毛却永远歉收——”
“我是诗神的孤儿,我那么新鲜陌生如句子/滴血的文字在推土机碾压下迸发。/我写什么,我又修改什么,/剧痛的文本像九级的地震,内伤的/国家我如何告诉你我的痛……”
在巨大的敌意面前,诗人对理解的渴求甚至胜过正在追寻的信仰。在这特定的时代,我们的精神底色多少都被污染了,就像雾霾布满的天空。写到这里时,我正在北京,听说这里半年晴空,半年雾霾,而我们呢?是不是永远活在晴雾交接时分的那一群人?
与敌意对抗的结果,是迷失。您试图在《酒魂》里寻找自己的图腾,这是一个多么疯狂的过程,从呐喊到抵制,精疲力竭后又再次去追寻。其实,图腾也是虚无的,它永远都在变,做一个停下来的诗人是多么难。
高先生,也许诗人走到末路后,最大的敌人反而是诗。
“游客更换了一茬又一茬/是因为我更频繁地制造自身的/废墟,一日千古的视听超体验是因为/诗的重建。推动文字中一切进化的那个魔力/渗透到脑部某个部分,并在其中放射光明,/这光明本身就是诗意,这光明所反应的情况就是哲学/不同的部分承受的多少也各不相同。“
诗歌的诞生,是诗人的胜利,也是下一次失败的到来。我们有太多值得去敬重和纪念的墓碑,可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我们有自己的影子,影子是不可复制的。语言是情感的产物,不是吗?高先生。
狂躁不安,让我们的眼睛都在天上飘着,几乎忘记了情感和语言的关系,就像树永远要扎根土壤一样的关系。不理解情感的人永远在呼吁要把诗写短。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明白,要怎样浩荡的一口气才能写出如此长诗,也更不明白要怎样浩荡的一口气才能写好短诗……
(细雨是轻描淡写之诗,最肤浅,却最讨人喜爱;暴雨是情绪饱满之诗,最激烈,却未必被世人理解。小雪是冷到外表之诗,精致小巧,世人误以为是诗之极品;大雪是冷到骨头里之诗,能冻住世间万物,人们却闭不出户,少有人能领略其风采。)
“我为这个古怪的星球创造的一个古怪的解禁日开始了/这一天遇见的人都是陌生人,每个名字都来自天空“
谢罪Vol.05伍/
“我要做一件严肃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涂黑,为了一部大诗歌的生日,我必须把自己涂黑”
这是您与李白的第一万席。两个在不同空间和历史中行走的人终将坐在一起。管它黑白还是其他颜色,管它左右东西,诗人脆弱,却不是妥协产物。人性本来就是通神的,只是那些装聋作哑的人,害怕看见鲲鹏在飞,闭口不提泣血的凤凰,可如果缺少了仰望,兽性也会抢占人性的……
“一直想找个人来一场真正的对话/每一个都很忙碌,不肯好好停下来/就像没有一辆救护车停下,历史突然变色”
高先生,肉体的痛苦不算什么,肉体消逝,一切都消散了。精神的毒素才是后患无穷的。天一般大小的绝症不会因为死而终止,它会继续散播,生长进每个人的骨髓里。是应该好好谈谈了,在放逐路上,我们都是身患恶疾的人,诗、酒、月亮让我们变成了瘾君子,在不断恶化的病情中开花。
许多人喝酒都不敢尽兴,怕醉态显露人前,其实,是诗人还是流氓,一醉便知。我爱饮酒,也喝醉过几次。在我看来,如果《酒魂》的前五章还算微醺的话,那么第六章开始就已经开始大醉了。大醉未昏,是人与天地鬼神最相通的时分。
真是可惜,每次喝醉都有诗意迸发出来,却因头晕脑胀而拿不起笔,但那种思维开阔的感觉,对一个诗人来说,可能比海洛因还容易上瘾。
“一个诗人胆大妄为捏造了一场酒气熏天的革命”
宋江醉酒,向浪里白条张顺例数各路豪杰,这是他将来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的资本。高先生的醉酒,则是在演义古今事,划分十天干。这等豪迈的激情,怎让人不动容?尽管“激情”在这个时代略显贬义,那是因为俗人们的激情都被大风和乌云所掌控,听风就是雨的激情,不过是无用的喧嚣而已。
“今夜我必须在场/今夜,神必须逃离高岗,今夜我必须胆大包天/不动一兵一卒,不掀翻一桌一凳/不碰飞任何一条大江大河/今夜我必须把这碗不惊动任何时空的大海/一干二净。”
也许,诗本身就是诗人的鸿门宴。我们不知道项羽是谁,整个剧本里的演员都在变动,只有项庄一直在舞剑。诗人也不知道自己的樊哙何时会冲进来,就像突然杀入瓶颈期的灵感一样,可这一切又是为了新的诗作。新的诗作代表着一场新的鸿门宴,自我复制一定是无效的,生死线上的惊心动魄只会发生一次,那些把鸿门宴复制成地摊货的人,拥有满街熙攘,却早已被项庄刺中。
活着的诗人,继续独自赴宴……
“今天我必须自生自灭,对我的孤独谢罪”
……
说了这么多,酒也醒得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来谈谈评论这件事了。
高世现先生通过长诗《酒魂》试图创造一种个人的、自我的精神史诗,并在文本中验证了通过个人精神与巨大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容量达成某种联系的可能性。这对当前诗坛盛行的个人化写作如何突破“小我”具有借鉴意义。在诗坛普遍强调现场感、参与感的情况下,高世现试图探索出一条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激活诗灵感的渠道,能够让诗意有血有肉地展现出命运的宽度,不再将目光集中在一次事件以及将文本意义依托给背后的解读,以一种不断挑战语言边界的方式进行对历史和现实的整合干预。
这首诗的长度是非常令人畏惧的,所涵盖的意象点和事件点也让人眼花缭乱。不过,这几万行诗里都透露着一股“气”,这是作者个人的野心和意识色彩自发的能量。作者在文中对自己的孤独、狂放、善意、愤怒和正义,以及人类的各种隐痛、无奈、追求和对困境的思索等各种大小情感与古今历史人物、事件、文化传统进行了有效结合。这是一部以酒为名,却实为借酒还魂的大作。我们可以感到作者强力有的诗句犹如鞭子一样抽打在身上的剧痛,也可以看到一个落魄文人在无尽的大路上饮酒高歌的身形。
不难看出,这首长诗吸收了大量当代诗歌的精华,与其说作者在文中写的是古人和自己,不如说是作者在扮演多个角色进行对话,这场对话旷古绝伦,从当代到古代都被涵盖其中,以一种强悍地姿态闯入历史剧本。而镜头式的切入,又让我们身临其境。作者在驾驭语言的同时还给予我们足够的立体感。多种艺术的混合让我们品尝到了一次盛大的精神盛宴。历史诗歌语境与现代诗歌语境的冲突又结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审美取向。
作者本人曾经说过:“我的诗歌理想,是不断在诗行之上寻找属于‘我的自传性线索’。”从文本中,我们还发现了作者对古老中国的“怀旧”以及人性中大彻大悟后的“野性”。这种“野性”,不是仅仅停留在语言上的暴力,而是思想深处的暴力,内部信念所赐予的暴力。在这一点上,作者可以说是将诗性的暴力发挥到了极致,纵观古今的豪迈中也展示出作者极强烈的狂欢主义色彩,而这正是我们现代诗歌中所缺少的。千万不要把诗性的狂欢和诗歌活动的狂欢搞混,这是一个人的天性决定的,无可复制。
(以上四段字全部为模仿修改,有自己的心里话但多是套话。)
其实,读完《酒魂》后,更多的是唏嘘。诗人的狂放离不开当代背景的重压,这让我不得不感到心疼,高先生。“我们活在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句话被无数人拿来装过逼,仿佛自己很高深莫测。可看穿这些人,一次诗歌活动就够了,我很讨厌对诗人的论资排本,看文本就够了,联合国主席未必就是好诗人,不是吗?可对于诗来说,我更喜欢一个人在诗歌中的情感和格局。至于理论层面的高度、深度、亮度等等,我认为都不重要,宗教、科学还是灵异也无所谓,诗就是诗,不是解剖学,诗人的情感可以融化任何事物,不是吗?
写到这里,突然感觉前面的几千字都是废话。一种挫败感开始蔓延了,好像前面的几千字真的已经死了。也罢,它们表达了我想表达的,没有违背自己,别人看不看得懂已经和我无关……
今年初写完《逃亡记》以后,感觉非常累,我很久没再写像样的东西了。我无法理解写诗还能感到很快乐的人,打着灵魂的名义糊弄自己,真的那么好玩吗?
高先生,就写到这儿吧,再写就有点失控了。最后,请允许我引用您的两句诗作为结尾,这也是我现在心里所想的。
“喝下这杯毒酒,我变成哑的算了,哑的”
“干了这一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毒酒/以一个最无耻的死者为这个时代写祭文,每臻绝唱。”
马晓康
年7月-年9月北京
马晓康,男,年生,祖籍山东东平,留澳七年,读书,写作,兼做翻译。参加过鲁迅文学院山东中青年作家研修班、浙江第三期新荷作家训练营和首届山东青年诗会,系第八届星星夏令营学员、《中国诗歌》第五届“新发现”夏令营学员。出版有诗集《纸片人》等。长诗《还魂记》被《山东诗人》秋季号首发后被《诗选刊》年12期中国诗歌年度大展专号转载,“诗客”北京最好白癜风专业医院治疗白癜风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