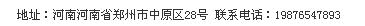治疗方案
连载岑寂如风
点这里回顾第四章
点这里回顾第三章
点这里回顾第二章
点这里回顾第一章
Chapter
5
我出生在年,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几个伟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相继去世,文革结束,东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越南统一,苹果公司成立。在一系列大事件的衬托下,冥冥中也注定了我的不平凡人生。”
听到她说起这些个名字事件,我才第一次从她身上感觉到年代感。但我始终认为她是喝多酒了想编故事。
“三十年前八月底,那一年我七岁,家里有个哥哥刚升入离家几十公里外在县城的初中,寄宿制的学校在开学前一天就有诸多事情,父母放心不下第一次离家的哥哥,打算陪着哥哥一同前去报道。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母亲一手拎着脸盆洗漱用品还有些吃的,另一只手挽着哥哥,父亲则扛着装满衣物的蛇皮袋,还有一床捆成炸药包模样的棉被。我目送着他们离开,我哥临走前对我说:“在家听话啊,我周末就回来。”父亲说:“我跟你妈可能晚点回来,中午你自己做饭吃。”
往常半个小时一趟的小客车那天也准时地到达我家门前不远处的小马路上,载上我的父亲母亲和哥哥,一秒都没多停留,关上车门就走了,哥哥靠窗坐下,打开窗户探出身子笑着跟我挥手,父母没有座位,隔着玻璃窗也向我摆手,示意我赶紧回去。我站在原地,目送着车尾喷薄着焦灼的气体消失在我视线。”
说到这,她停下来往杯子里倒酒。我望着她,见她眼睛里闪动着光亮,那是眼眶里含满了泪水却没掉出来的剔透。
“如果,我那时知道那将是此生最后一次和他们互动,我一定会玩儿命追上那辆车…”说完她极其微弱地哽咽了一下。若不是我仔细地观察,很难察觉出她脸上这个细微的举动。至此,我才打从心底严肃起来,她并没有在跟我开玩笑编故事。
“那天晚些时候,大约中午时分,我在家里给自己准备午餐。有邻居跑到我家来,神情紧张吞吞吐吐地跟我说:“妹仔,上马桥出事了。一辆小客车因为行驶在桥上时爆胎失控翻到桥下,整车人摔下距离桥面几十米高的干枯河床,半数的人当场死亡,其中,包括你的哥哥和爸爸,你的妈妈身医院了,你赶紧去看看。”我还来不及反应就被邻居阿姨抓上了下一班开往县城的班车。医院我完全没概念。没有哭闹,没有恐惧,只觉得一切都像是在梦里还没醒。直到我看到躺在急救间里满脸血迹的母亲,才吓得尖叫起来冲过去抱着母亲嚎啕大哭。可惜,连母亲也听不到我的呼喊了。她手里死死攥着八十块钞票,其中一张面值五十的钞票上用血印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一个医生告诉我,那是母亲在急救车上意识模糊时叫人帮忙从口袋里掏出来,用手指沾着身上的血渍写下的,并嘱咐一定要交到她女儿手里。我接过那张钱,人生第一次,懂得什么叫天塌了。”
指尖的烟快燃烧到尽头。她停下来摁熄了火。我着急地问:“钞票上写着什么?”
“好好。就两个字,好好干什么呢?母亲没念过什么书,会写的字不多,也或许是想写却来不及了。但我懂得那未能表达出来的意思,那是一个母亲在弥留之际还惦记着自己唯一幸存的女儿,希望她能坚强的,好好的,活下去。”她眼里仍闪着光,只是没了刚才强忍着的液体。
“对不起,我不知道在你身上竟然有这么悲惨过去。”听到这里,除了满腹的同情,我已经完全词穷。如果这是她为她曾经的工作经历做出辩解,那一刻我没办法不理解,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就面对如此巨大的家庭变故,还有什么不值得谅解。
“那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九月,原本我也该开开心心的入学,也因此不得不拖延下来,因为在大人们料理完父母亲及哥哥的后事,另一个紧迫的问题摆在面前,我的抚养问题。外公外婆爷爷都已经过世,奶奶年岁已大独自一人还耳聋,显然无力抚养。那时在我们那个地方福利院机制并不完善,政府鼓励像这样父母双亡又没有直系承担的孤儿最好由亲戚代为抚养,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离我最近的亲戚是住在县城里的姑姑,姑姑家没有孩子,再适合不过了,但姑姑并不情愿,在县政府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尤其是姑父的坚持下,勉强同意了。那时候,虽然我内心也不愿意,也排斥,但我仍感激姑父的善良慷慨,不至于让我流落街头或是成为孤儿。我在九月下旬就搬到他们家,次月就被安排进入已经推迟了一个月的小学校园。姑姑在县城粮油站有份保管员的工作,姑父在自家经营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家庭条件算得上不错的他们俩却没有要孩子,因为姑姑不喜欢孩子,我知道姑姑对我很冷淡,但好在不讨厌,姑父对我很好,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在这个新家庭里的生活,谈不上开心,但至少渐渐步入正轨,我努力试图把父母的爱分一点在姑姑姑父身上,毕竟他们让我活了下来。”
说完这一句,她又稍事停顿,我始终注意着她神情的变化,虽然很细微,但我感觉得到她突然的眉头紧锁。
“半年后,我渐渐感觉到每次洗澡的时候都有人在偷看,一开始是从自行打开的门缝,我学会锁门后。就变成墙顶上方小小的透气窗,我原本以为是姑姑不放心可能会看一眼,后来有一次我直接撞上了那双眼睛,那眼睛没有回避,仍目带凶光地看着我,我认出了那眼神里的坚决,就如始终坚持要抚养我的那股决心。那时的我不懂得要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只好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但一次两次,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并且从一开始小心翼翼变得越发明目张胆,我的心态也有了转变,当我再感觉到目光如电而来,我再也不故意躲闪,故意遮掩。想看就看个够吧,就当作是报答他的收养之恩。”
听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冷颤,我想起了那个她突然站在露台上对着遥远的我脱得一丝不挂的夜。原来并非心血来潮空穴来风。
“我以为最糟糕的情况不过如此了。谁能想到那只不过是我人生悲歌当中的序曲而已。我的房间是姑父家原先堆放柴火的杂物间,简易的木门只有一个小小的木栓,只消一把刀片一样的工具就可轻松从外面把门打开。一个凛冬的夜,黑暗中有人悄悄打开了我的房门,爬上了我的床,当我惊慌失措地醒来,一张满是胡茬子、烟臭味和酒味的嘴巴在我的脸上盲目地乱蹭,直至在黑暗中寻到我的嘴,并一口包住,使得我没机会发出声音来。手被一只粗糙的大手反手按在头顶,除了身体还能扭动,几乎动弹不得,接着衣服被掀起,裤子被扯掉,再来是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从身体下方迅速直达大脑,几乎觉得要痛到晕厥过去,但我仍攥紧拳头想要以此借助些力量来反抗这一切。显然,一切都是徒劳,小小的身躯被压在一个庞然大物之下,就像被大象踩住的蚂蚁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挣扎无果后我放弃了抵抗,我以为我活不过那个夜晚了,就任由那令人头皮发麻的疼痛一阵阵袭来,一阵阵撕扯着身体。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湿糟糟的东西抽离出我的身体,随之而来是一句低沉恶狠的警告:“敢说出去,我就打死你。”便消失在黑暗里。打从我懂事起我就听母亲说过我是个特别自爱的女孩子,从三四岁起,除了母亲,不让任何异性给我洗澡,哥哥都不行。而那晚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懂那是什么行为,只是觉得被冒犯了、恐惧、以及让人反胃的恶心。待确认姑父已经离去,我的身体才开始后知后觉地发抖抽搐。我以为是太冷了,我拉回被子把自己裹起来想寻回些许温暖,却发现无论如何都捂不暖身体,还有心。那一年,我七岁。”
她语调极其轻松,听不出半点沉重悲伤的意味,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平淡到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很难想象这些年她究竟是如何平复内心的怨愤。我却控制不住像打寒战一般一阵阵发抖,我捏紧了拳头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发现于事无补。我知道现在提出离开一下非常的不合适,但我别无选择,胃里翻江倒海我必须立即消失一下。
“对不起,我去个洗手间。”不等她回答,我就起身一路小跑进洗手间,冲进马桶间连门都没来得及关就抱着马桶狂吐不止。我深知不是酒精的原因,但就是觉得恶心,深深的恶心。恶心什么呢?我不知道是因为她的故事,还是因为几个小时前我竟对着早上刚给她拍的照片而打飞机,我的行为与那个老男人有什么区别呢,同样令人作呕,我止不住地狂吐,想把席卷全身都罪恶感统统吐出来。
等我收拾好,站在洗手池前望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不知道何去何从,我觉得我没有勇气再坐回去面对她,我想干脆从后门一走了之算了。可是那样真的太残酷,此时的我难道我不该是回到她身边借给她个肩膀靠靠给予她一丝丝温暖吗?最终我抬起铅块一样沉重的步子回到了座位上。“见笑了,酒喝多了。”我故作镇定的说道。
“你还要听吗?”她看看我,又看看手里的酒。我很感激她终于知道询问我的意见,如果可以,我多想说不,但我会意到今天是逃不掉的,她那渴望倾诉的眼神,我没办法说一个不字。
“噩梦般的生活还在继续,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过去找我奶奶,可是你能指望一个又老又聋的老太太做什么呢?我深知这是件并不光彩的事,但我不敢告诉警察,因为时常有穿着制服模样的男子在姑父的杂货铺逗留,抽烟打牌,每次我见到他们,他们脸上都带着邪恶的笑,我总觉得他们和姑父是一伙的。我更不敢学校的老师,我怕我一说可能连书都没得读,我才上小学一年级,不上学将来我该怎么办,我不能连这唯一可以短暂逃离梦魇的地方都失去。我也不敢告诉姑姑,我不知道告诉她的后果是什么,姑父是不是真的会打死我。我甚至想,要不就死了算了,可是我怕死,我答应了母亲要活下去。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我强迫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把这当成生存的代价,毕竟那个男人提供我吃,提供我住,还让我读书。我想,等我长大了,再大一点点,我总能想到结束这一切的方式。再后来,我就习惯了这种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一次在某个黑夜里被酒味烟味熏得睁不开眼的嘴巴包住,被一根湿糟糟的东西绞碎着身体的生活方式。当我越长大,越懂得这个行为叫做什么,但我无能为力,我对生命充满了好奇,我想知道老天究竟要我怎么样。我对知识也充满了欲望,深知唯有以此作为武器才能改变现状。我必须要读书,也必须活下去,所以我只能满足他,讨好他。我在无数个无法入眠的黑夜里告诫自己再忍忍,一切总会过去的。”
听到这里,我已忍不住湿了眼眶,眼前这个女人在本该属于天真烂漫的年纪竟有着如此之多令人无法想象的无助。但她始终都没有哭。
“升初中的那个暑假,当我满心期待着新的学校新的生活,我的腹部和下身开始剧烈的疼痛,即使在他不来骚扰我的日子,也异常疼痛难忍,有一天直接痛到晕厥过去。等我再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私人诊所里,我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只觉得自己完完全全被掏空了。一个可怜我的小护士偷偷告诉我,这辈子都我不会成为母亲了。那一年我十二岁。这件事并没有让我痛苦万分,那时的我并不懂得成为一个母亲于一个女人的意义,我只想身体快点好起来,去新学校,去开展新生活。我相信结束这三年多少学业,事情一定会有转机。”
“第二年下半学期,转机就开始显现了。家里突然多了一个成员,姑父的侄子要升学,因为户籍的原因需要回到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于是从外地回到县城,跟我在同一所学校的高中部读高三,学校离家近,因此也寄宿在姑夫家里。”
“那是个清秀的男孩子,个子高大,身材精壮。留着清爽的寸头,一对浓密的眉毛显得人格外精神,大大的双眼皮衬得眼睛深邃有神,牙齿很白,咧嘴一笑还有半个浅浅的酒窝。很阳光,很帅气。姑姑让我称呼他为哥哥,其实按辈份算,我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总之年纪居大,叫哥哥总是应该的。见到他第一眼,我想起了自己的哥哥,就莫名有股强烈的依赖感和安全感,觉得救星降临。事实上,他的确是我的救星,因为我们的房间就一墙之隔,不像离姑姑姑父的房间远远离着一间堂屋,太近,细微的动作都能听到声音,因此姑父就收敛了许多,几乎有半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在深夜时悄悄潜进我的房间。我与哥哥一起上学放学,吃住都在一起,不知不觉变得亲密起来,渐渐的,我发现自己身上前所未有的变化,每每看到他就脸红耳热心跳加速,看不到就莫名焦躁。有一天晚饭后请他帮我讲解一道物理题,我们并肩而坐,他侧着头极认真地向我讲解着,时不时问我懂不懂。哪里能懂,这么近距离看着他的脸我根本没办法专心起来,画一个图线时他突然站起身来绕到我的身后,俯下身子用他的右手握住我右手带动着我画起来。那一刻,让我人生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爱恋。我爱我的父亲父母,爱我的哥哥,可是对他,那是一种超越了其他一切情感的迷恋。一来二去,我发现自己并不是单相思,越来越多的眼神触碰,我能感受到他眼里饱含了和我同样的爱意,只是多一份克制,毕竟于他而言没有什么比全力以赴投入升学考试更重要的事。我没有打扰他,默默喜欢就好,能天天看到他,和他站在一起就好,我祈祷着时间慢一点再慢一点,因为我害怕那场考试结束之后,我的生活会一如从前。
年的六月,他结束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高考,一出考场,他兴奋地跑来找我,说有事情要跟我讲。我坐上他的单车后座往县城外的郊区骑,初夏的味道让人心旷神怡,路边第一拨播种下去的油菜种子已经开花了。自从七岁离开自己村子,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田野的风光。他把我带到一处视野开阔的油菜花田里,丢下单车,拉着我的手往花田里钻,突然,他转过身一把把我拥进怀里,并说道:“岑青你知道吗?从我见到你第一眼就喜欢上你。”我趴在他的胸口听见他强有力的心跳,霎时眼泪掉了下来,这大概是自父母去世后第一件让我感到开心的事情,我喜欢的人也喜欢我,没有比这更让人有幸福感。我抬起头满含深情地看着他,心里有千言万语想对他说,但我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我不想说出任何一个破坏气氛的话语破坏现在的气氛。或许是我的沉默让他意会到我的心意。他把我扶起来,双手扶着我的肩头,身体慢慢在靠近。我知道他想吻我,我也想用无比幸福的吻迎上去,可是看见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嘴唇,我下意识地躲闪了,脑子挥之不去是那张满是胡茬烟臭口臭的嘴巴。我内心拼命努力想甩开那个令人作呕的梦魇,可是我做不到。他感受到我的不安,立即停止了冒犯。我多么怕我这一躲就失去了他,我赶紧主动把手搭在一起他肩上把他勾住,略带抽泣地说:“带我一起走吧,去你上大学的城市,我可以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好不好?好不好?”生怕他会拒绝,我连续问了两遍。他看着我问:“你确定吗?”我玩儿命的点头。回去之后,虽然我们极力掩饰,但亲密暧昧的感觉还是毫无遁形地自然流露出来。我们商量好等他一放榜,他就先回,我随后离家出走跟过去。”
“你跟他走了吗?”我趁她停下来喝酒的间隙着急的问。
“放榜后,他以六百多分的成绩顺利考入他的第一志愿西南大学。在他准备离开的头一天,那是一个周末的早晨,姑姑有事出去了,哥哥在房间收拾自己的东西,姑父把正在厨房准备午饭的我拽到哥哥房间,我一路心惊胆战,难道有什么事情败露了?姑父已经很久不怎么白癜风好了治疗白癜风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