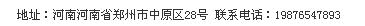疾病分类
锃亮的耳朵
《文学港》年度优秀作品大展
锃亮的耳朵
一
早晨起来,觉得哪里不对劲,像是睡闷了。上班走在人车互不相让的大街上,不由自主跺跺脚,又跺跺脚,我想跺出我体内的寒、体内的神,精气神,瞧初冬的早晨一切是多么地透明。中午下班走在斑马线上,在左右扭头看人看车的空隙,脚不由自主又跺了几下。路过一个小型广场,中午的小广场没有什么人,人都压在马路上,我环绕着广场慢走一圈,太阳很好,不由自主又想做那个动作,跺脚,我想我这是怎么了,脚怎么了。
我忽然明白一个事实,我的脚步声没有了,脚在寻找它的声音,这是一个新鲜事件。这么多年,影子、脚步声,还有我,我们三个三位一体,从来没有分开过。瞧,影子是多么地忠实,即便是我远行,即便是我中弹,它都默守着我脚下的土地,没有谁能拽走它,或割走它一块。还有那脚步声,它一直在明示或是暗示我,你的双脚多么有力,你还很年轻,你还有很多很多的路要走,脚步声就是明证。
现在,我成了一个没有脚步声的人。我把远方弄丢了。
我那么谨小慎微地走,我还是丢掉了东西。在人生的旅途上,我是不是开始走一路掉一路,掉一件少一件了呢?
我从包里掏出手机,又有几个未接电话。
耳朵呜呜的,一直在呜呜的。好多声音从我的耳朵旁边跑掉了。它们无视耳朵的存在。我的耳朵拉不住它们了。耳朵开始有意识地找它们,从大街、从广场、从树下、从旮旯,找它们回到耳朵里去。
我开始爱幻想起来,幻想有一天,在我早起的某个时刻,耳朵一激灵,声音“嗡”地一声飞回来了,或者在我使劲吞咽之际,耳朵一激灵,声音“嗡”地一声飞回来了,或者像我曾经的一次军事打靶,在扑地一声之后,耳朵惊晕多日,多日之后声音在外游荡够了,觉得在外游荡也没有什么意思,终又悄悄地溜回到我的耳廓。
耳鼓涨涨的,有什么东西在向外推送,小心翼翼地一串一串向外送。有时我按按,在我按住的当下,它们马上停住了。它们懂得适时收手。
就这么顶住了七日。七日之后,终觉该去见见医生。
在经过了一连串的检查之后,医生看着我的检测单,他很平静地告诉我,你得了神经性耳聋。
就这样得了神经性耳聋!
医院的大门,心里迸出一句话,你的耳朵叫驴毛给堵住了。这是我们乡下骂人的一句话,经常是骂不听话的孩子的,耳朵叫驴毛给堵住了,而不是说被棉花给堵住了,想是驴毛更厉害些吧。现在我的耳朵就被驴毛堵住了。我千辛万苦从乡下走出来,小时候的诅咒还是如影随行地应验到了我身上。
我把脚步声弄丢了,我把手机声弄丢了。不久我还要把喇叭声弄丢。这些车子早上吵、晚上吵,这以后你们还吵给谁听。你们也有噤声的时候。
还有楼上打孩子的声音。哭声是从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嗓子里发出的,夜晚经常是一声赛过一声,可以听得出打他的那个父亲一点都不手软。那是一对农民工夫妇,我白天看过他们,头发都是乱乱的,一幅没有精神的样子,夜里打起孩子来精神倒十足得很。多少次我停下笔来谛听,我想我应该去把那男孩子领回来,告诉他们家人说,我这里正好多一张桌子,我可以和那个男孩好好谈一谈。但是我不是他们家什么人,那个男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打量我?世界上最晦暗不明的目光莫不过如此,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也莫不过如此。
还有我的对门,近日我在家总是听到一连串钥匙的声音,接着是一个五六岁小女孩的哭声,爸爸我实在学不会呀,我实在学不会呀。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一点也不着急,他说,再试一下,再试一下,一定能会。还是那个小女孩的哭声,爸爸我实在开不开,我开不开门。接着又是一连串钥匙响动的声音。
这个女孩的父亲或是母亲,在夜里的时候,不知是谁会偶尔嗷地先叫一下,接着你嗷一下,他嗷一下,像扔砖头似的,一块一块对扔过去,所幸不久就停住了,想是屋里的砖头准备的不够充分。
这些声音本来就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我把这些声音统统还给他们。以前我在他们面前装着自然,装着不知道他们的任何事情,现在我更坦然、更放心地走自己的路了。只是我以后还能不能知道,那个学开门的小女孩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打开自己家的大门呢?
至于屋里的声音,坐在马桶上,电水壶尖叫的声音。刚把双手湿进水里,手机催命的声音。
从今后再也没有这些刺耳的声音。
窗外再也没有风声、雷声、雨声、下雪的声音。天上该下什么下什么,那是天的事情。我的耳朵再也不屑管这些事情。
也再没有生的声音、死的声音。棒喝的声音。正义的声音、非正义的声音。
也不要再考虑什么是分贝,它们到底有多大量的分贝。
大海的声音,花开的声音,露珠滴落的声音,心跳的声音。这些心底的声音,它们会不会也被带走?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不要碰我的耳朵。现在心中只有这一个声音。
晚上睡觉前,把手机定好闹铃,把这东西端端正正地放在枕头边,不知道它明天是否还会准时叫醒我。
这个用声音和我保持联系的家伙,不知道以后它将怎么过。
夜里睡觉,梦到过一次带血的耳朵,那是凡·高的耳朵。
还梦到过一群人在跳舞。我听不到她们的脚步声,她们也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
我以后会干什么呢?我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能变成莫扎特吗?
二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神经性耳聋?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似乎也没有吃过药物。
染过一次发,是不是用了毒药水?是不是吃了毒大米?以些类推,还有毒牛奶、毒馒头,毒鸡蛋、毒蘑菇、毒红枣……上次吃过一次螃蟹,人类把该吃的东西吃遍了、吃完了,连这么丑陋的东西也不放过,螃蟹藏在污泥里,螃蟹一生气浑身长毒,人类一吃到它们,耳朵呜地一下就背过气去了。这是螃蟹唯一能做的事情。
再或者就是近年才流行的“雾霾”“沙尘暴”这些个词捣的怪?电视里天天都在播放空气指数。每到一个季节,田野里的秸秆总是明明灭灭,有人点火,有人灭火,有人被关,有人被放,电视、报纸上每天都在为这个事长篇累牍报导。人的两眼照例流着泪,嘴巴咳嗽咳嗽的,嘴巴一咳嗽,耳朵一生气,两耳一背,什么事也不问了。嘴巴不能不议论,因为嘴巴咳嗽着,报纸也不能不报导,报纸需要增加发行量。耳朵不再想知道了,耳朵不听不行吗?上帝开始揪驴毛堵一些人的耳朵了。
也或许是我自己的事。我家的巷口,有一个卖盒饭的,白铁皮手推车里,有红油烧的鱼、红油的茄子、红油的豇豆、大块的红烧肉,那个穿着白大褂的姑娘总是麻利地给别人盛菜,歪着勺子舀一下、又歪着勺子舀一下,多次才把泡沫饭盒点满,她似乎是舍不得多给,但又得把泡沫盒子装满,她就这么点啊点的,每回用电子秤秤完报过价目后,勺子又都故意地给饭盒里再点一次,好让别人心知肚明,她向饭盒点勺子的频率极高,也很好看。我每次就是她这么点啊、点的,用一个塑料袋子装着,提着菜一盒、饭一盒上楼去了。
后来自是好长一段时间不买她的饭菜了,也还是日日从她家手推车门前过,我有时在观察她,看她接电话的手是不是迟钝,我有时也在观察我们小区里的人接电话的手是不是迟钝,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也像我一样,揣着手机,没事人似的,专等着别人急吼吼地来提示。
如果有一天,刚好在我走过她家的白铁皮手推车前,忽然有人没收了她的家伙、她的饭,或者某一天她的手推车忽然不见了,墙上贴着一张告示,她的手推车被公家整治了,她被查出使用了地沟油,那么好了我的心就终于放下来了,瞧瞧,终于被我猜对了,早就觉得她的态度那么谦卑似乎在包藏着什么。可是我日日从巷口走,她日日在我面前点菜,用勺子挖一下,点一下,又用勺子挖一下,点一下,没有穿制服的人来收拾她,人们还照样用一个塑料袋装着菜一盒、饭一盒走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近日去了一趟九华山,别人去理佛,我也跟去了,我去拜佛,我这一拜,佛一高兴,我的耳朵啊呜一声就好了。从山上下来,坐在车里,耳朵呜呜似乎更厉害了,我用手揉着耳朵、摸着耳朵,心想佛也不管我了,佛什么时候会管我。车子里坐得挤挤的,一个孩子坐在母亲的腿上,母亲不时按住他的腿、他的手,不让他手舞足蹈,孩子的嘴也不闲着,他的母亲大喝一声道,瞧把你阿姨吵的,把阿姨的耳朵也吵聋了吧,看阿姨不打你!我一向还怀疑,我这耳聋是不是大街上的声音吵聋的,这母亲的言论,却给我的耳聋另开辟了一条思路。但我没有苟同,我的耳朵可以聋,孩子的心灵不可以玷污。
我像放电影似的日日把这些东西无声地过一遍,又过一遍,我急切想揪出其中的主谋。他们是如何对我下手的,我想弄清事实真相。
总之,我认为耳聋了,是我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住了不该住的环境,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不久母亲到我家。母亲终于知道了我耳聋的事。母亲随口就做出了结论,冻的,肯定是冻的,你想你天天坐到半夜,坐得浑身冰凉,耳朵能好受吗?耳朵一不好受,不聋才怪呢!
我愣着神想了一会,我长时间地坐,颈椎会痛、坐骨神经会痛、胃会受凉、五脏六腑会受凉,凭什么耳朵老是热乎乎的、直棱棱的为你服务?耳朵想通了,耳朵想体现自己的重要性,耳朵呜地一下子背过气去了。
这是我听到的最直接,最不容置疑的结论。谁又敢肯定它不是元凶呢?
三
以前对于未接电话,我给人家的解释是,哎呀,真不好意思,手机在包里没有听见。
或者是,哎呀,真不好意思,我听到手机铃声了,手机在包里就是找不到。
现在我给人家的解释是,真不好意思,我得了神经性耳聋。
朋友对我得了神经性耳聋,首先是不相信。瞧瞧,眼神既不空洞,也不飘忽,甚至嘴角还挂着笑,怎么会就得了耳聋了呢?怎么看也不像啊,谁得你也不能得啊。
还有的朋友是惊奇之后,表示了极大的热心,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放宽心,能治好,该吃就吃,该喝就喝……
还有的朋友是大手一挥,说,没事的,没事的,能治好,现在除了癌症,啥病都不是病,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没事的,我摊上大事了,这倒霉的事叫我摊上了。什么叫能治好,我都吃了两个多月的药了,耳朵还呜呜叫。你这么急吼吼的样子,根本就没有心思就这个问题和我谈一谈。你这是不关心我,不爱护我,心里眼里没有我。你这是草菅人命。
还有的朋友态度是,不就是呜地一下耳朵背过气了吗,不要理他,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说不定哪天,耳朵呜地一下又回来了。你要是得了这个病,你就不会说这个话了,我现在是站也不是,睡也不是,那个呜呜的索命似的跟着我。再说,你怎么能知道声音就一定能找回来呢,它跑远了、跑丢了、到处找我找不到怎么办。你这是误导我,你这是不负责任。你这是让我过一天是一天,过一天少一天。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其他的朋友就不这样讲。有的朋友说,用双氧水洗,洗过后再涂酮康唑,这个软膏一涂就灵。临走了,还不忘叮嘱一句,一定要试试。过几天还要打电话询问,涂了没有。还有的朋友说,去吊水,吊青霉素、吊头孢,一吊就管用。他们不劝我“怎么活不是活”,他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当下。他们不劝我草草度日。我把这些都当救命稻草似的收藏着,哪一天医生对我失望了,或者我对医生失望了,它们就该派上用场了。
针对我的这个病,我的朋友无一例外的都劝我,要吃好喝好,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这个问题说到核心上去了。自从我得了病,就再也不知道啥叫吃好、喝好了。
朋友们聚会,要给我倒酒,我说我得了神经性耳聋,不能喝酒了。一圈人都在叫,倒上倒上,酒能活血,一活血耳朵就好了。经过几轮推搡好不容易达成协议,倒一小杯看着。一小杯看完了,人家端着一杯酒站在你面前,人家“滋儿”一声下去了,你说人家能放过你吗?刚才一开始说自己胃出血的那个人也不再坚持了,那个说自己痛风的人也不再坚持了,桌子上一开始还说有得胰腺炎的、口腔扁平苔藓的,那个手里提着一个大水杯,杯里装着黑乎乎的保肝护肝药的,现在也不再说我有病了,一桌子都是满上满上,走一个走一个。
人活着就应该是奔着快乐去的,谁能拒绝酒赋予我们的快乐呢?谁能阻挡我们奔向快乐的步伐呢?
吃完饭回来后,我疑心耳病又加重了,或者本身并没有加重,但疑心也是一种病。
后来我再外出吃饭,我不说话了,躲在一拐角。既然不喝酒,还叨叨啥呢。我埋头吃东西,吃完了盘盘碟碟杯杯盏盏,再吃主食。吃完了主食,人家正喝在兴头上。人家正说得兴高采烈,人家活在天堂里,你坐在小板凳上。你们无话可说。你们活在不一样的世界里。别人嘴都在动,你的嘴已经动完了,你的嘴只能闲着。别人白天清醒,而你呜呜独醉。现在别人沉醉,唯你独醒。你说你这是什么人生。
后来别人再叫我吃饭,我支支吾吾推三阻四不去了。因为我坐在那里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吃,我还能怎么吃。现在我才知道拥有一双好耳朵的吃,才是色香味俱全的吃,才是世界上最动人的吃。
不出去吃了,偏偏又知道谁和谁围在一块吃。人家吃得热气腾腾、妙语连珠,人家一晚上云里雾里的。你说你一个人在家,默不作声捧着一只碗,整晚都蹲在黑影地里,吃什么能吃好、喝什么能喝好呢。思前想后,日子越发回到过去一般。
自从我得了这个病,我和我朋友之间的关系变了。虽然他们中有的人仍试图对我很好。但是我正在远离他们,我正在泊去。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一锅老汤,那味道渐渐寡了、淡了。
四
我听到过最美妙的声音,那是任何一双好耳朵都不曾听过的。
医院治疗。我歪着一边耳朵接受光束探测,然后又歪着另一边耳朵接受光束探测,光束肯定没摸索到什么问题。年轻的医生给我开了一张单子,叫我到听力测试室。在听力测试室,护士把我关到一个小玻璃房里,给我带上耳麦,吩咐我说左耳听到声音举左手,右耳听到声音举右手,她把玻璃门关上,坐在对面遥控我。耳朵还没有全聋,当然还能听到声音,叮的声音、嘟的声音、当的声音、嘤的声音,声音那么小,怕惊醒我似的,只是那么小心地害羞地盯着我一下,小心地神圣地电击我一下,它像微小的颗粒,仿佛拿着抹布轻轻一擦就能擦掉。
那是夏夜星光灿烂,大地深处发出的声音。我轻轻俯下身子,把耳朵贴在树叶上,我继续俯下身子,把耳朵贴在大地上。翅膀抖动的声音,真空盘旋的声音,叶子落下的声音,踩踏树枝的声音,一只小虫子被打搅的惊讶声。或是根本就没有声音,只是萤火虫的萤光一闪,只是小虫子的虚恍一枪。我不敢抬起脚,抬起脚就踩灭二亩地的声音,抬起脚又踩灭二亩地的声音。我甚至不敢咳嗽,怕惊跑了它们。
我不停地举左手,举右手,或是忘了举也不尽然。我听得太认真了,有时忘了自己的存在,有时忘了大地的存在。
我以为此生仅有幸聆听一次这样天籁的声音。医院接受治疗。我拿出我们市的结果单,省城医生不看,他让我再听一次。也许他认为我听得太噪杂、也许他认为我听得太不可思议,或许他认为我举手举得太迫不及待、太不合适宜。总之他要我再听一便。我珍惜这样的机会,老老实实又听了一回。
我记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我上次聆听的时候发生的。我正在聚精会神地寻找大地深处的声音,如果我不找,它们就会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统统消失掉,我抢救性似的,找一个是一个,忽然手机爆炸似的响起,我想把手机的声音捂住,事实上是赶快地打开了接听功能,我要和天籁之外的声音对话。护士忽然发现了什么,她大喝一声,你怎么能听电话,赶快放下!经这么一闹腾,你说多少声音走形、不翼而飞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做心电图,在打印机将打未打、即将输出结果的时候,忽然手机响了,那个时候我接听手机,心跳得不正常,我不接手机,心跳得更不正常。这天外的声音,粗鲁得近乎无礼,但是我们又都无时无刻不带着它、惦记着它,生怕搞丢了它、慢待了它。似乎只有它在,我们的生活才纳入正轨。可是有了它,我们的生活又哪一天安顿过呢,医院也不例外。我们需要被它唤醒吗。
和这最美妙的声音能相媲美的,我以为是瑜珈养生益智功的声音。“让我们选一个最舒服的姿势,盘腿坐下,现在请将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体上,由内到外去关心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让你的呼吸越来越慢,越来越深……并且在整个练习过程中保持这种呼吸方式……”我最喜欢瑜珈的最后一节,“让我们轻轻地仰卧下来,请你闭上眼睛,放松你的面部表情,把你的双脚分开30公分左右,让你的脚心放松,让你的脚背放松,……让你的小腿、小腿肚放松,让你的膝关节、大腿内侧放松……让你的骨盆区域得到充分的加强和滋养……”
假如能在这种声音里静静地睡去,让夏日深夜里嘤嘤嗡嗡的声音萦绕耳畔,让这些声音轻轻轻轻地贴近你,让它们感受你的呼吸、你的心跳,这多么好。再也不用为耳朵的前途担心了,也不用担心自己能不能成为莫扎特了,也不用担心自己成为游离的一分子了。这个被驴毛堵住耳朵的女人,这个生活总爱给她搞点恶作剧的女人,这个听到过最美妙声音的女人,心安理得得像一个婴儿,她静静地躺去,她将不再接受任何考验。她躺成遗忘,躺成骸骨,躺成大地的一部分,然后和大地上的声音融为一体,这又有什么不好。
五
坐火车到另外一个城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这是个和我生命有关联的地方,这些年来我反反复复坐着这趟火车去看和我生命里有关联的人。
这次坐上这趟火车去看医生。为治疗耳朵已经浪费了太多上班时间,且这回是每天都要去针灸。为此我请半天假,上午在单位上班,下午去治疗。亦即是中午坐火车走,治疗完毕,晚上坐火车回来。第二天中午再坐火车走,晚上再回来。没有比抢救一双好耳朵,更让人活得有耐心。以此类推,人在危难之中,想拽自己一把的愿望多么强烈。
火车还躺在铁轨上静静地等我。这趟火车哪个车厢我没坐过?甚至有的座位是重复坐过,有的地点是重复站过的,甚至整列火车每个座位我都有可能目测过、染指过。我又走进这列火车,车厢里浓重的带着酸味儿的气息又熟悉地“嗡”地一声向我扑来,基本上照例又被呛得一个趔趄,但站稳脚跟,一会儿适应就闻不到了,如果有座位的话,一会就会觉得有一种暖暖的美好。这回是站着的,两个车厢之间的吻合地带,似乎吻合的不是很好,地板在脚下扭来扭去,带动着身子也在扭来扭去。车厢照例很嘈杂,即便我耳朵出问题了,我还是能感觉到它们的嘈杂程度一点不减。车厢里坐着是坐着的,站着是站着的,照例是腿贴着腿,腿靠着腿。腿边都是行李,行李架上也是行李。车厢里每个人都捧着一部手机,他们都紧紧捏住自己的声音,每个人都神情庄重木然。
我听挤在我旁边的三个姑娘讲话。一个姑娘讲,就这样回去,怎么和家里人交待啊。另一个姑娘说,没办法交待也得回去,早上八点钟干到晚上八点钟,不被主管管死才怪。第三个姑娘说,再干下去,耳朵就被振聋了,不给钱也得走。三个姑娘一时陷入沉寂。我听明白了,这三个姑娘在厂里干不下去了,不给工钱,也卷铺盖回家了。除了每个人一个鼓鼓的包,也没见什么行李。我忽然觉得我们市的老板有点太抠了,她们就这么空荡荡地回家。我突然又突发奇想,以后耳朵要真不行了,我是不是适合在这样的地方干活,瞧,耳朵再也不怕被吵了,多大的声音也不是问题了。这三个姑娘给我提供一个新的适合的地方。但我不愿往深处里想。一会儿一个姑娘说,瞧瞧我回家还给孩子买了新衣呢,她一定会高兴坏了。另一个姑娘说,我也给孩子买了吃的,他最喜欢棒棒糖了,不知道他还认不认我。另一个姑娘说,马上要到家里了,我要找小学同学到小吃街大吃一场。她们像是马上要扑到家的样子,一会又说得兴高采烈起来。年轻真好。不像我因为一双耳朵,弄得就像活不下去似的。
我另一侧还有一个姑娘,她和那三个姑娘就不一样。她一上车,挤好站立位置,带上耳麦,就开始“播报”。她双眼低垂,面含微笑,音量适中,语气温软适度,她在对自己讲。比播音员讲得动情多了,并且始终不看我们,身边再多的声音都不是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声音能打断这个源源不断的声音。火车一直在开,这个声音一直在延续,火车也需要这样的声音。世界也不能缺少这样的声音。在这样的声音里,人人都是美好的。即使有一天我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能看到这样一个美好的场景,我的内心也是湿润润的。
我的膝盖还抵着一对人儿。男的坐在一个大麻包上,两眼红肿,头发蓬乱,半截身子趴着车窗向外看。他的对面是一个女子,半卧在一个麻包上,伸长两腿,扭着半截身子,也是趴着车窗向外看。他们漫无表情地在看,似乎车厢里任何声音和他们都没有关系。因为是冬天,车窗外面是黄一阵、褐一阵的大地。如果有一天我听不到了,我是不是和他们一样,也把一车厢里的人都丢在突如其来的寂静里,自己睁一双茫然的眼,在茫然地逡巡着。
突然我听到一声雌性的雄壮的声音:“你说我和谁在一起,你说我和谁在一起,我和一屋子的男人在一起!”抬眼望去,可不是一屋子男人嘛,尽管也有很多女人,但这样有突出地讲,也是可以的。我差不多突发性地笑出声来。抬眼望去,这是一个面色红润、中等个头,身材结实的微胖女子。她被挤在人群中间,她把手机贴近耳朵,正在很有情绪地讲:“你说我干什么去了,你说我干什么去了……你说我能上哪,你说我能上哪……”感谢我的耳朵,它让我听到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甚至有史以来最能让我笑话的一句话。如果没有这一句话,在以后再也生不出波澜的世界里,我靠什么来回暖生温,靠什么取悦自己。
和这个“和一屋子的男人在一起”的女人一同下车。跟在她身后走了好一阵子。甚至有了某种心灵上的依恋。
六
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因这耳聋意外而更走近了一步。
从我有记忆开始,父亲就不停地揉自己的耳朵,一侧一侧地揉,光照在脸上,脸一侧一侧抖动、变形。
父亲年轻的时候面部受过伤。那是年的春天吧,全国广播事业大发展,各乡村普及广播、喇叭。在水泥预制场他和同事们一块“大炼”电线杆,一根一根水泥电线杆需要急切地从县城列队到麦田、到大队部。他搅拌水泥、挥汗如雨,钢筋在模板里越拉越直,他不知道他一生的厄运就此来临,钢筋不小心崩断了,正打在他面部的三叉神经,他当即血流如注。医院的。我当时在院子里跳皮筋,跳得一头是汗不肯停下,不明白他出了怎样大的事,也不医院,更不知道他后来都到过哪些地方治疗。只知道他后来回家了,变得不再是我们印象中的爸爸了,他变成了一个我们不敢相认的人。
再后来就是耳鸣,宿命似的一生跟着他。医院。想弄聋自己,想去死。他不能睡觉。这些话讲过多少年,我们都听习惯了,习以为常了,也就不是事了,大家都照常过日子,大家不再问他怎么过日子。
他以前爱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事,喜欢直呼我的大名,仿佛这样更显得郑重。但他声音大得吓人,我在办公室给他回话,他在那边用大号声音回我,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后来我跑到走廊给他回话,再后来我跑到卫生间给他回话。我给我母亲讲,以后家里有事,你给我打电话,我找不到地方给他回话。母亲牢牢地记住了我的这句话,以后不论是谁给家里打电话,母亲总是快步抢前,接电话成了她的专利,而他只能看一眼了。后来我们给他们配了手机,两个人共用一部机子,手机一直掌握在母亲手中,他不再有对话权,他也就更不乐意摸那个东西一把了。我的一句抱怨的话,让他在这个世界站立的位置又向后退了一步,他从此不再给我打电话。
耳聋招人嫌。有一次我回家,正好在一楼街道边碰到他们,他俩正准备一块出去办事。母亲眼尖一下看到了我,先是和我打招呼。父亲却揣了钥匙,一个人向前奔了。母亲在后面喊他,我在后面喊他,想是那天风大,风把我们的声音又都吹回来了吧。要不,他怎么能不闻不问,一个人一直向前跑呢,父亲一向走路的速度并不快,那天不知怎么了,似乎是脚不沾地地行走。也许没有比目的地更为重要的事情了吧。世界一向把父亲丢在后面,这回是父亲把我们俩丢在后面。我希望能有什么事情止住父亲的脚步,但那天父亲一个人一直在向前走。
我以前回家,先给家里打个电话,要是母亲接,这个家立刻可以回。若是我顺路回去,这个家能不能进,还待考证。我在门外喊开门,我在门外重重拍门,我给屋里打电话,门不认识我,门不给我开。我打母亲手机,母亲说在外面这就回去。母亲到了家门口,拿钥匙开了门,父亲在屋里稳稳坐着。
我们和母亲说话,然后再用大一号的声音翻译给他听,他常常站在外围,微微伸着头专注地听,似乎我们说的是天下头等大事。他有时也会插一两句嘴,但常常是因为插得时间、地点不准,常常把我们弄糊涂了,我们都不知道下句该说什么了。他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刚才说得热闹,现在又不说了。
我母亲就骂他,你这个聋子。有时我们觉得这样骂他,也不亏。后来也还是觉得有点愧疚。
现在我也和他一样了,伸着头、专注地听别人说话了。也许不多久也有人这样说我,你这个聋子。
我现在试图了解他,他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他过着怎样的生活,他谦和的外表下,都掩藏了些什么。不如把自己弄聋了、不如死了算了,是在一种什么的状态下说出的,几十年来一夜一夜睁着眼,那是一个又一个什么样的夜晚。这一切我们所知甚少,甚至绝少想过。他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面露笑容的生活。
而我一直想背叛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这样想。远离他、背离他。做一个和他完全不一样的人。
对他而言,这个世界过于宏大,而他似乎还没有准备好,他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个世界,去处理他身边有关的事情。对突如其来的事情总是手足无措。不爱说话,不知道如何和别人交往,害羞。怕参会发言,怕照相。别人找他的事,他竭尽全力,而他断然不肯找别人帮忙,那是求人,他有极强的自尊。实话实说,不圆滑。他抱怨自己,办不好事情,在儿女面前也抱怨自己。并且不奢望被家人原谅。他想突破自己的核,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能为儿女谋福利,能让妻子不操心的人,他想让她们过上好日子。但他做不到。想有一个强有力的父亲的心愿一直伴随着我们少年时期,直至长大成人。
他有一个丰富的内心,一生热衷编书、写书,毛笔字钢笔字遒劲有力,这些字似在表露着他无法言说的愿望。在听力衰退了以后,他不再能倾听世界,他更热衷倾听文字,他找到了更适合他存在的世界。他有丰富的感情,但不表露,似乎说出来是一件不合适宜的事情。他的眼睛温纯善良,直到老年,眼神里亦有孩子似的天真。他就坐在我的对面,隔着三十年的光阴我打量着他,他带着老花镜专注地看报纸,我们终无法自如交谈。
我反省自己,想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希望自己独立,精明而干练,能独挡一面,让人心悦诚服,让人心生爱慕。而事实上是,我亦垂着长长的胳膊,无力地看着这个世界。无言,无助。不愿意让陌生人走近,不加陌生人QQ,不和他们说话。对待好的人和事,不肯攀附,亦不肯俯就。内心不安定,没有安全感。压抑。希望随遇而安。渴望朋友,但不愿主动示好。若有感情,必他(她)先给。孤独,在情感的世界里自给自足。眼睛温润,时常为些小事流下莫名感动的泪水。若有风暴,内心却能做到波澜不惊。我和世界没能妥善相处,和自己没能够妥善相处,我以为是他没有教给我怎么做。
我终放弃了对他的抱怨,时光教会我学会忘记。我和他重新融为一体,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什么能比对方给予我的抚慰更能管用。没有谁能够伴我们度过漫漫冬夜,伴我们度过一年又一年,除了他们。
我坐在椅子上,他教我揉耳廓、捏耳垂、敲耳鼓。他想把他一生对付耳朵的经验传授给我。他身上的某个疾病也必将在某个时候在我身上呈现,如足踝上的几个白癜斑。有一个年老的父亲睡在隔壁,他在前面引领着我,教我不慌不忙地应对疾病,教我不慌不忙地老去,这是一件幸福而又心安的事情。
有时候他站在阳台上,看着窗外,揉自己的耳廓。我站在客厅对着镜子也在揉自己的耳廓,并且长久审视这艺术品一般的东西。母亲看着我说,你和你爸越来越一模一样了。
这话要是专门针对父亲,母亲的话里肯定暗含一种贬义,这话说给我听,母亲的话里就有了一种我至今还没有品味出来的深意。
父亲,这么多年你不在我眼前,我一个人在外离你很久也很远,但我终究没有长成别人家的孩子,我终究和你一模一样了。
我们雷同的耳朵应该生活在天堂里。
现在,拥有一双锃亮的耳朵,走在马路上,我的成就感,我的幸福感是无法言喻的。